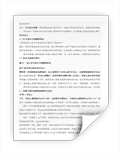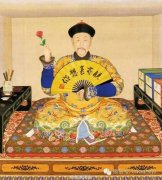故宫文物修复师:工作时聊个天都不行(组图)(2)
采漆基本在比较容易出漆的三伏天进行。因为害怕白天漆被太阳晒起皱,割漆一般都在晚上。从深夜十二点到第二天黎明,闵俊嵘经常只戴一个头灯在漆黑的没有月光、伸手不见五指的山峦里作业,下面是陡峭嶙峋的山峰,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坠下。
按照一棵树十个口割四十刀,一宿割六十棵树来算,有的时候六七个小时下来也就能装一矿泉水瓶那么多的漆。所以行业里流传着“百里千刀一斤漆”的说法。
这些只是开始。为了修复好一把所有构件都翻开、上面的漆都脱落殆尽的清宫旧藏、国家二级文物金陵易少山斫古琴,闵俊嵘花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为了修这把琴,他还专门买了一把斫琴学习乐理和演奏。9年时间,一直坚持学习。“修复过程中,不能违背古琴基本的演奏功能。如何演奏自己也得懂。”闵俊嵘说。
刚刚过去的春节,闵俊嵘就是在故宫度过的。除夕当天走在空无一人的故宫,这个工作了十二年的地方仿佛又有了第一次来时那种皇家大院的感觉。一进来,外面的声音似乎都消失了,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要心静 工作不让闲聊令新人郁闷 师傅批别太飘

王有亮最近接收了一些香筒的修复任务
早晨七点半,迎着晨曦,王有亮沿着高高的红墙拐了几个弯,在故宫西侧一扇安装了门禁的小门前停下,开锁。
门的侧墙上挂着漆黑底金色字的牌子:“故宫博物院科技部”。因为风吹雨淋,牌子边缘的地方已经发旧,依稀露出斑驳的底色。
从这扇门进去后,还要再经过十扇门,王有亮才能到自己办公的地方——青铜器组修复室。吱的一声,门开了。院子里的三只黄黑斑点的猫见到有人来,殷勤地跟在王有亮身后。他从屋里拿出猫粮,倒在地上。它们一边吃一边摇着尾巴,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新的一天开始了。
王有亮今年52岁。从职业高中毕业之后,他就被分配到这儿工作,一做就是32年。为了把青铜器表面磨得光滑,需要用很大的手劲儿,“有的时候磨得指纹也没了,手上都是茧子。”
最难受的是过滤铜绣的时候。漫天的铜末子飞到身上,遇到出汗,鼻子、脸甚至全身都是绿的。空气中弥漫着铜锈的味道,“闻多了鼻子、嗓子、眼睛都特别难受。”王有亮说。
由于常年要接触各种化学品,青铜器组修复室的人大多都有鼻炎。每当换季或天气转凉,都是他们最难受的时候,鼻子不适会一直打喷嚏。
最大的挑战是对性格的磨砺。“刚来那会儿年轻人嘛,欢蹦乱跳的。”19岁就到故宫工作的王有亮经常会因为中午休息的时候出去溜冰或者游泳而被师傅批评。
刚来没几天,师傅阴着脸对王有亮说,“别这么闹,你性格不能太飘,沉不下来做工作就不稳当。”
“有的时候甚至说话也不让,两个人想要聊个天都不行。”这让那时特别爱玩的王有亮着实郁闷了一段时间。
如今在故宫看到的栩栩如生、莲花上站着展翅欲飞仙鹤的莲鹤方壶就是由王有亮修复的。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是全国一级甲等文物。莲鹤方壶四个字是由郭沫若为其定名的。
初送来时,方壶的器腹裂开不规则形状的大口子,耳朵也掉了一个,仙鹤看上去“奄奄一息”。从焊接耳朵、拉铜片补配腹部参差不平的口子,到往上做旧,王有亮开始一步一步地修复。
其中做旧调色是最难的。“上色特别容易看出毛病来,你觉得是绿,但一上去马上就能看出不一样,有的时候甚至睡觉时都在琢磨加多少啊、是加点蓝啊还是加点红啊?”
半个多月的时间,一件青铜器的稀世珍宝在王有亮的手中“活”起来了。他说,如果不出意外,这件青铜器至少一百年都不用再修。
“现在自己一步一步稳当多了,之前年轻时的那些想法也都没了。”王有亮说。
“安全癖”也成了王有亮、闵俊嵘等故宫文物修复师的职业病,“就是你永远怕文物倒。”例如,放置文物的时候得反复检查一下,防止发生意外。
文/丽案调查工作室 实习记者 丁雪
本版摄/记者 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