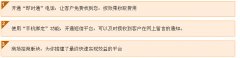东楚网·黄石新闻网
东楚网黄石新闻网(黄石日报)□ 赵时学 前不久我从《读者》杂志上看到一篇《“健忘”趣谈》的文章。文中介绍了几位健忘者的趣事:一位著名学者向朋友介绍自己的夫人,他用手指着妻,却半天说不出她的名字,只好向旁边的同事请教。还有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教授,他有一次打电话给陶孟和教授。对方的服务员问他是谁,他一时答不上来,说:“不管他,请陶先生接电话就行了”。谁知对方非要报一下姓名,他只好请教拉洋车送他来的王师傅。王师傅回答:“只听别人称你金博士”。一个“金”字提醒了他。
读了这篇文章想起了我自己。他们忘掉的我都忘过,他们没忘掉的我也忘过。这不是夸大其词以哗众取宠,而是真的,有事实为证。
20多年前的秋天,我从武昌乘火车去昆明,在车厢内与一个乘客谈得很投机,谈到激情时,突然间问我贵姓,我说了个“免贵……”以后竟答不出姓来。幸好一时间脑子灵活起来,反问他贵姓,想岔开话题。说来奇怪他姓赵。这一下提醒了我:“我俩是家门。”真是天赐良机,没让我丢丑,否则会被人误认为精神病院的“逃犯”了。
有个星期天我去罗四聪家,他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之一。从读私塾时起我俩就是同窗,后来又一起读中学,算是同桌、同床、同席、同行的“四同”好友。工作后虽然分隔了20余载,后来又碰到一起,时常交往。这一天从他那儿回来,下车时碰上另一位老同学问我去了哪儿,我回答去了老同学家。当他问我去哪一家时,我竟然说不出。只把对方俊俏的面容,热情的个性,和善的心肠详述了一遍。不料这位老兄也猜不出来,说:“你讲的这位老同学我也很熟悉,只是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来”。说来好笑,两个健忘家遇到一块儿了。最后我想起了我去的这位老学友是我们同窗中常说的一句话“他是我们班上的老班长”。这才提醒对方,他说是“罗四聪”。那么这一位对方又是谁呢?直至现在仍想不起。
我不仅生活上的事儿健忘,教学上的健忘也不逊色。写黑板字不是多手多脚就是缺膊断腿。有一堂历史课讲王安石变法,我却大谈“百日维新”,大赞谭嗣同被害时,神色自若,慷慨高歌:“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大无畏精神。学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所以我认为(仅属感性认知),健忘有两大原因:一是大脑中记忆功能出了故障,我属于这一类。二是心不在焉,生活上的事马马虎虎,工作上认认真真。
下面举个健忘教授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前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有位世界知名教授——伊里奇,也是一位稍有知名度的健忘教授。有一天晚饭后,他把儿子放在婴儿车里推出去散步,途中遇上了他的老同学,两人亲热攀谈两个多小时后回家了。一进门亲切问妻子“咱们宝贝的儿子睡了吗?”有一次他开小车去100里外的地方办事,事毕后他排了两个小时的队买一张长途车票回家,翌日上午上班才发现车丢了。有一次为了查阅资料他问一位要好的老教授国立图书馆的电话号码,老教授跟他开了个玩笑,把伊里奇家的号码“338—825”告诉了他。当他的夫人问他有什么事时,他颇为不解“咦,她到图书馆干吗?”这位教授真能评上吉尼斯世界健忘大师了。
然而他在教学上一点也不犯糊涂。他上课不要教材,不用教案,像一部留声机滔滔不绝,津津乐道,学生们听得入了迷。每逢引经据典时,都要指出来自何书、何版,甚至哪一页。有一天他将打印好的试卷丢在了家,就口述考题让学生作答。学生怀疑他口述有误,事后与考卷查对,三、四页之多,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错。他有惊人记忆力,也能登上吉尼斯世界纪录。这种人你能给他加顶桂冠——健忘大师?
类似这样的人我还能举出两个,一个是我心爱的妻子,一个是我的同事汤老师。好了就写这多,多了会有人说我是婆婆妈妈,唠唠叨叨了。
(作者单位:黄石纺织机械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