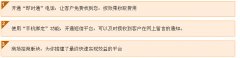焦循与李斗交谊趣谈
扬州戏曲文化史上的“双子”星
——焦循与李斗交谊趣谈
同处清中叶的著名学者、戏曲理论家焦循与曲论家、戏剧家李斗颇有交谊。两人除了直接交游往来,辄作文字交,其友谊诚笃,情真意挚,具备共同的思想基础。焦循、李斗无疑是清代扬州文坛艺苑璀璨夺目的“双子”星座,各以其独特贡献和丰厚遗产充实、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宝库。今年是焦循诞辰二百五十周年、李斗诞辰二百六十四周年,谨以此文聊表纪念。
清代乾嘉之际的著名经学家、数学家和戏曲理论家焦循,与以《扬州画舫录》名世的同时代曲论家、戏剧家李斗友善。焦循(1763-1820),世居甘泉县黄珏桥镇南焦庄(今属邗江区方巷镇),嘉庆六年(1801)举人,渐淡于仕进,家居著书自娱,终老于乡。李斗(1749-1817),祖籍山西忻州静乐县,明崇祯末年高祖移居扬州郡城,后占籍仪征,诸生,一生未为官。焦循小于李斗十四岁,两人同属扬州府,声息相通,辄有交往,且多作文字交,传为文坛佳话;他们又都是各有创获的戏曲理论家,堪称扬州戏曲文化史上的“双子”星座,其戏剧艺术观既有相同、相似之处,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个性和明显的差异性。
焦循为李斗《扬州画舫录》题诗
清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正月,阮元督学山东,邀族姐夫焦循游幕。焦循启程前往济南,时闻老友李斗《扬州画舫录》将成,特题七绝诗一首以示祝贺。诗序曰:“将之济南,留别李艾堂,即题其《扬州画舫录》。”诗云:
太平诗酒见名流,碧水湾头百个舟。
十二卷成须寄我,挑灯聊作故乡游。
此诗是焦循在扬州还是赴济南途中所作,不得而知,按一、二句诗意,很可能是应“名流”时任山东学政的阮元之邀,登程在扬州湾头乘船出发时作。诗中可见他难掩对《扬州画舫录》即将问世的喜悦,和推重此著留别李斗时嘱托书成“须寄我”,以一慰其山东之行游子乡愁的迫切心情。《扬州画舫录》是李斗“自甲申至于乙卯,凡三十年”(自序),“考索于志乘碑版,咨询于故老通人,采访于舟人市贾”(阮元序)而精心结撰的小百科全书式著名笔记,洵为清代康雍乾时代特别是乾隆极盛时期扬州文明的实录,社会经济文化辉煌的缩影。《扬州画舫录》书成刊刻前后,时贤纷纷序跋题咏,一时曾“洛阳纸贵”,从焦循此首题诗的称誉中亦可略见一斑。另一方面,味“十二卷成须寄我”诗句,也可知《扬州画舫录》十八卷在乾隆六十年尚未全部刊刻成书。据其际稍后甘泉杨炤、如皋吴嘉谟等人题诗考知,《扬州画舫录》实际成书付梓当在清嘉庆二年丁巳(1797)间。
《扬州画舫录》关于焦循学术成就的记载
李斗《扬州画舫录》刊刻成书时,焦循正是三十四岁左右风华正茂的青年才士,在经学、数学、曲学等领域的研究皆已突飞猛进取得不俗成就。对此,《扬州画舫录》有多处载述,并不乏赞扬之语。
《扬州画舫录》卷十三中概要简介了焦循的学术业绩:
焦循字里堂,北湖明经。熟于《毛诗》、《三礼》,好天文律算之学。郑兆珏、郑伟、王准皆与之游。所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三十卷、《毛诗释地》七卷、《群经宫室图》二卷、《礼记索隐》数十卷、《焦氏教子弟书》二卷,又有《释交》、《释弧》、《释轮》、《释椭》、《乘方释例》、《加减乘除释》,共二十卷,皆言算术也。
上述简介,展示了青年才俊焦循的经学、数学等学术研究已始有博大气象且具有坚实的蕴涵。诸多硕果无可争议地表明,焦循的确是乾隆后期扬州学人中的佼佼者,也预示着他必将成为嘉庆时的学术中坚,以及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良好前景。
《扬州画舫录》卷五指出,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年间“以修改词曲来扬州”的著名学者凌廷堪,“通诸经,于《三礼》尤深,好天文、历算之学,与江都焦循并称”,“里堂称以歙县凌仲子、吴县李锐尚之、歙县汪莱孝婴为论天三友”。该卷又载有凌廷堪与焦循论弧、三角书、焦循与李尚之书、李尚之答焦循书三信全文。李斗云:
予于推算之学,全无所知,获与仲子、里堂交,每闻其绪论……予按推步之学,梅(文鼎)氏、江(慎修)氏、戴(震)氏为最精,而仲子、里堂、尚之三君,复推其所不足而有以补之。
引文中言推步(算)之学,即谓推算天象历法之学。李斗详细引载凌廷堪、李尚之与焦循讨论弧、三角和推步之学的三信内容。可窥知三学人之间切磋学问、交流学术心得之一斑,以及其严谨治学可贵的学人品格与诚笃的友谊,足见焦循在数学和天文、历法领域已臻于较高造诣;同时明示李斗与焦循之间的交谊也是不薄的。
值得注意的是,《扬州画舫录》卷五还以占全卷三分之一强的篇幅转载了焦循已佚论著《曲考》所考元明清杂剧、传奇、元末南戏、清代花部剧等共一千零四十五种。其中载焦循考黄文旸《曲海总目》九百七十九种(李斗误记为一千零一十三种),焦循增考杂剧四十种、连厢词二种、传奇二十四种计六十六种(李斗转载误为“其杂剧四十二种,传奇二十六种”),因而保留了焦循逝世后久已亡佚的早期曲论专著《曲考》部分内容珍贵资料,李斗功不可没。此外,《画舫录》卷八、卷十五分别记载了焦循收徐复为弟子,“授以《毛诗》、《周官礼》诸经”,培养其成才的事迹和焦循《贞女辨》上、下篇全文。
《岁星记》传奇焦序和晚年李斗“防风馆”得名由来
李斗作有《奇酸记》、《岁星记》两部传奇剧。前者有乾隆六十年刊本,以小说《金瓶梅》故事情节,用意秉承张竹坡评点的“苦孝说”;后者系嘉庆八年冬李斗应扬州东园主人之请为元宵灯节所编,敷演西汉文学家东方朔的故事。《岁星记》取名于《列仙传》“东方朔为‘岁星’之精”,情节完整,主角东方朔在剧中角色行当三变,相貌三变,服饰由儒服而官戴、仙装,全剧文武相间,悲喜穿插,排场热闹,正适合过年喜庆的气氛。李斗才思敏捷,不数月即完稿付伶人排演,于嘉庆九年元宵节在东园正式上演。焦循特受李斗之邀欣然作《岁星记》序,考述以东方朔为主角的剧本创作源流,作出此剧足可比肩前人的高度评价,并记载了李斗兼做导演指导排演的情况。
《剧说》原稿本卷三,“余尝憾元人曲不及东方曼倩事”一条删去了以下一段文字:
李艾塘作《岁星记》传奇,余为之序云:岁乙丑(清嘉庆十年,1805),访李君艾塘于防风馆,见其近作《岁星记》传奇,本《列仙传》东方朔为“岁星”之精也。夫曼倩在孝武时,文章不让相如,谏诤同于长孺——二句本方正学先生。班生专为列传,而明辩当时所传奇言怪事之非,则“岁星”之说,为孟坚所不信。然而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一代非常之人,未有不钟毓于星辰河岳之灵者。曼倩之为“岁星”,何独不然?艾塘此作,可与升庵、孝若、笨庵诸曲比肩伯仲,夫又何疑!艾塘此记成,旋付歌儿,较曲者以不合律,请改。艾塘曰:“令歌者来,吾口授之。”且唱且演,关白唱段,一一指示,各尽其妙。嗟乎!论曲者每短《琵琶记》不谐于律,惜未经高氏亲授之耳。汤若士云:“不妨天下人拗折嗓子。”此诨语也,岂真拗折嗓子耶?
焦循《岁星记·序》提供了他与李斗两位文友交往的宝贵资料。焦循此序在考探剧本创作源流后,认为斯剧可与明代戏剧名家杨慎(升庵)、茅孝若、孙原文(笨庵)所创东方朔题材诸戏曲“比肩仲伯”,予以赞赏,又记述李斗悉心指导、参与排演,以其“且唱且演,关白唱段,一一指示,各尽其妙”和“《琵琶记》不谐于律,惜未经高氏亲授”,来充分肯定李斗精通音律。焦氏序论符合部分实情,不过有溢美之评。李斗确实熟悉填曲、剧本结构、舞台排场乃至表演,尤善音律。但其曲词音律仍有不合剧场流行唱法之处,“须他自己作特别处理并不断讲解示范,才能使演员掌握,这实在毫无必要”,“防风馆客评《奇酸记》有云:‘至于引子、尾声,实在歌者难工,读者难解,信乎其道不易讲也’”,“评者意在赞扬,却也道出了‘难工’的实情”。而总观李斗所作《奇酸记》、《岁星记》两部传奇,“其创作立意不新或纯为应景,内容平庸,故舞台演唱不广,只能在众多剧作中聊占一席而已”。(以上引见明光《扬州戏剧文化史论》第322页。)
李斗晚年以疾食防风而愈,名所居为防风馆。前所述“防风馆客”即当为李斗自署。李斗参修盐法志,曾“卧病盐法志馆久矣”,一度病重殆危,幸后有老医李翁诊治制“防风(药名)粥进之,得生,遂以(防风)颜馆中所居之室”,因而此诗集亦名《防风馆诗》。李斗患重病生命垂危,焦循十分关切,得知其病愈,又为之庆幸,且在长篇传记《李翁医记》中记载了李斗两次得病和治愈详情始末,与李医先后诊断、疗治的简要病案,交代了“防风馆”得名的由来。其文曰:
李艾塘痛疝,医温之,不应。翁诊曰:“阴雍也。”用半夏汤通之,愈。明年,病腹痛,翁适赴河帅召,客淮上。他医以为湿,治以茵陈,病益剧,将死矣。翁归,急视之,令服防风粥,已而下白粪如银,病顿已。李遂名其屋为防风馆。
焦李交谊的重要思想基础:都道“花”、“雅”争胜
焦循与李斗都是清代乾嘉时期卓有成就的戏曲理论家。焦循著名论著《剧说》、《花部农谭》和李斗著名笔记文集《扬州画舫录》中卷五,都以较多笔墨热情洋溢地引载、记述、评论了扬州等地戏曲舞台上演出的雅部昆剧和花部多种地方戏剧的情形,是清代中叶“花”、“雅”争胜的真实反映。这也是焦循、李斗两人能缔有交谊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基于此,李斗追求演员表演神化、臻于“化工”、“化境”与焦循主张“优之为技”“善肖人之形容,动人之欢笑”先后呼应。李斗指出“元人唱口,元气漓淋,直与唐诗宋词争衡”,又对焦循在杂著《易余籥录》卷十五中提出的“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艺发展观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和启迪,焦循则较李斗有明显的拓展和超越,并对后世著名学者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胡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等人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深刻的积极影响。
囿于所处时代和个人局限,李斗未能像同一时代而稍后的焦循那样,顺应清中叶前后花部地方戏曲崛起、蓬勃兴盛,雅部昆曲日益衰颓,花雅并雄而花部渐胜雅部以至最终于清末取而代之诞生京剧的时代潮流。但从《画舫录》卷五所记录的弥足珍贵的资料中已透露出花部兴盛的些许信息,流露出作者的倾向性,显然是站在肯定亦同时推重花雅两部优秀表演艺术的立场上,即花雅并录,不褒雅贬花,而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尽管作为传奇作家的李斗,审美趣味当偏向于昆曲,可他并未以偏好为评价标准,而是将花雅并奏视为正常的艺术竞争和艺术生存状态,着眼表演艺术特征,只凭演技识高低,不以花雅论是非。这较当时一般正统人士和士大夫尊雅贬花的偏见,更显其客观公正,心态平和,体现出进步的平民意识和可贵的科学精神。而且他关于花部发展和艺术内容、表演特色等较为详细的记载,对戏曲理论家焦循的宝贵启示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