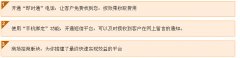吴冠中风景写生记趣(2)
每次到外地写生,画具材料必须准备得十分齐全。1978年到西双版纳,当时外地肥皂紧张,洗油画笔离不开肥皂,我带的肥皂有限,便分外重视,每次洗完笔,便立即将肥皂收藏好,洗脸从不动用。日子久了,总得洗一次内衣吧,洗衣总不能不用肥皂。但洗衣和洗笔时完全是两种精神状态,洗笔必须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洗衣服洗个大概就算了,往往还心不在焉。洗完衣服后突然想起肥皂遗忘在水池边了,洗笔时从来不可能遗忘肥皂,因肥皂的重要性只同洗笔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洗衣服时便忘其重要的身份了。我惶恐地立即奔到水池边去找重要的肥皂,不见了!
“脏饰”
1974年,我和黄永玉、袁运甫及祝大年从黄山写生后到了苏州,住进比较讲究的南林饭店。我们在黄山晒脱了一层皮,脸被风刮得枯涩枯涩的,头发蓬乱,背着那么多画具,一看就知是一群画画的。穿得整齐干净的服务员问:“你们中有画油画的吗?”他偏对油画感兴趣,永玉立即回答:“老吴就是画油画的。”服务员便转向我:“小心别将颜色弄脏房间。”黄山玉屏楼为游客备有出租的棉大衣,几乎每件棉大衣上都抹有油画颜料,招待所的褥子上也常擦着油色,画家太多了,油画家尤其讨厌!要学学我们宜兴的周处严格要求自己的作风,不让别人认为是一害,不让别人讨厌油画。我每次作完画,总用棉花将染在地上的颜料擦得不留一点痕迹。大概是在甪直的旅社里,有一回擦洗洗过笔的脸盆,用了许多肥皂和棉花还是擦不干净,怎么回事呢?仔细观察,那不是我弄上的颜料,原来那是属于脸盆本身设计中的色彩!是装饰艺术,不是“脏饰”艺术!
冰冻残荷与石林开花
夏天,北京的北海公园里映日荷花别样红,确是旅游和休息的胜地。我长期住在北海后门附近,得天独厚,当心情舒畅的时候或苦闷的时候,便经常可进北海去散步。“四人帮”控制期间的一个隆冬,我裹着厚棉衣因事进入北海,见水面都早已冰冻三尺,但高高矮矮枯残的荷叶与枝条却都未被清理,乌黑乌黑的身段,像一群挺立着的木乃伊。齐白石画过许多残荷,但何曾表现出这一悲壮的气氛呢,这使我想起了罗丹的雕塑《加莱义民》。强烈的欲望驱使我要画这冰冻了的荷尸,我想还应该添上一只也冻成了冰的蜻蜓。亲人和朋友们坚决制止我作这幅画,我没有画。
1977年我到云南石林写生,石林里都是石头,虽具各种状貌,但也还是僵化了的石头嘛!然而石林里开满了白色的野蔷薇,都是从石头隙缝间开出来的。“四人帮”倒台了,我心情很舒畅,倒台前知识分子们的心情能舒畅吗?我曾以为冰冻的荷尸正是自己的写照呢!我于是大画其石林开花,还题了一句款:今日中华春光好,石头林里也开花。
摘自《横站生涯五十年》吴冠中著文汇出版社2006年3月版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