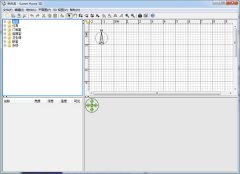钱学森鲜为人知的一面
手稿中的钱学森
一次,在中科院一位朋友的办公室。我去时,朋友在欣赏一卷《钱学森手稿》。说是欣赏,他眼中流露的正是这样的目光。这一套手稿,分两卷,五百多页,是从钱学森早期的手稿中遴选出来的。
我拿过来翻了翻,与其说是手稿,莫如说是艺术品。无论中文、英文、大字、小字、计算、图表,都工工整整,一丝不苟,连一个小小的等号,也长短有度,中规中矩。
钱学森的手稿令我想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进而想到他唯美的人格。
如是我闻:在美国期间,钱学森仅仅为了解决一道薄壳变形的难题,研究的手稿就累积了厚厚一大摞,在工作进展到五百多页部分,他的自我感觉是:“不满意!!!”直到八百多页时,才长舒一口气。他把手稿装进牛皮纸信封,在外面标明“最后定稿”,继而觉得不妥,又在旁边添上一句:“在科学上没有最后!”
考试中的钱学森
对于笔者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如下的几句老实话。回顾学生时代,钱学森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算是好学生,但每次考试也就八十多分;我考取上海交大,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国的博士口试成绩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
八十多分,第三名,第二等,这哪里像公众心目中的天才学子?然而,事实就是事实,钱学森没有避讳,倒是轮到世人惊讶,因为他们已习惯了把大师的从前和卓越、优异划等号。钱学森的这份自供,同时也纠正一个误区:一个人的成才与否,跟考试成绩并不成绝对正比。不信,可去查查当年那些成绩排在钱学森前面的同学,作些比较分析。
天才加勤奋的钱学森
钱学森的天才是不容置疑的。根据已故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采访,麻省理工的学子曾对他佩服不已。有一回,钱学森正在黑板上解一道十分冗长的算式,有个学生问了另一个与此题目无关、但也十分困难的问题,钱学森起初不予理会,继续在四个十英尺长、四英尺宽的黑板上,写满了算式。
“光是能在脑袋中装进那么多东西,就已经够惊人了,”一位叫做哈维格的学生回忆,“但更令我们惊叹的是,他转过身来,把另一个复杂问题的答案同时也解答出来!他怎么能够一边在黑板上计算一个冗长算式,而同时又解决另一同样繁复的问题,真是令我大惑不解!”
天才绝对来于勤奋。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一位犹太籍的校友回忆:“有天一大早――是个假日,感恩节或圣诞节――我在学校赶功课,以为全幢建筑物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把留声机开得特别响,乐曲高潮到一半时,有人猛力敲我的墙壁。原来我打扰到钱学森了。我这才知道中国学生比犹太学生更用功。后来他送我几份他写的关于近音速可压缩流体压力校正公式的最新论文,算是对于曾经向我大吼大叫聊表歉意。”
钱学森在麻省理工的一位学生麦克则回忆:钱学森教学很认真,全心全意放在课程上。他希望学生也付出相同的热忱学习,如果他们表现不如预期,他就会大发雷霆。有一次,他要求麦克做一些有关扇叶涡轮引擎的计算,麦克说:“我算了好一阵子,但到了午餐时间,我就吃饭去了。回来的时候,他正在发脾气。他说:‘你这是什么样的科学家,算到一半,竟敢跑去吃中饭!’”
胸怀宽广的钱学森
关于归国后的钱学森,这里补充两个细节。
一、你注意过钱学森的履历表吗?他是先担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然后改任副院长。这事不合常规,怎么官越做越小,难道犯了什么错误?不是的。原来,钱学森出任院长时,只有45岁,年富力强,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光。但院长这职务,是一把手,什么都得管,包括生老病死、柴米油盐。举例说,底下要办一个幼儿园,也得让他拨冗批复。钱学森不想把精力耗费在这些琐事上,他主动打报告,辞去院长职务,降为副院长。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集中精力专门抓业务了。
二、钱学森晚年与不同领域的后辈有过多次学术合作,在发表文章时,他常常坚持把年轻人的名字署在前面。这种胸怀与情操,在当代,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
硬汉钱学森
在张纯如的笔下,钱学森有着十分粗犷而任性的硬汉形象。譬如说,上世纪40年代初,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为一批攻读硕士学位的军官上课。他当年的学生们回忆,他上课总要迟到几分钟,正当大家猜测他今天会否缺席时,他快速冲进教室,二话不说,抓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开了,直到用细小而工整的字迹,填满所有的黑板为止。
有次,一个学生举手说:“第二面黑板上的第三个方程式,我看不懂。”钱学森不予理睬。另一个学生忍不住发问:“怎么样,你不回答他的问题吗?”钱学森硬邦邦地说:“他只是在叙述一个事实,不是提出问题。”又有一次,一个学生问钱学森:“你刚提出的问题是否万无一失?”钱学森冷冷地瞪了他一眼,说:“只有笨蛋才需要万无一失的方法。”
钱学森教学,没有小考、大考,也不布置家庭作业。课后,学生们只能绞尽脑汁地温习课堂笔记,那都是纯数学,一个方程式接一个方程式。期末考试,钱学森出的题目极难极难,全班差不多都吃了零蛋。学生找上级的教授告状。钱学森对此回答:“我又不是教幼儿园!这是研究所!”
个性钱学森
数年后,钱学森转到麻省理工学院,为航空系的研究生开课。在那儿,学生们的回忆同样充满恐怖色彩。诸如:“人人知道他是个自我中心的独行客。”“他在社交场合总显得惴惴不安,学生觉得他冷漠高傲。”“他是我见过的最难以亲近而惹人讨厌的教授。他好像刻意要把课程教得索然无味,让学生提不起兴趣似的。”“大多数学生不了解他,甚至怕他。我知道起码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学生,是被他整得流着眼泪离校的。”
还有更加不近人情的描述:除了上课,学生只偶尔在古根海姆大楼跟他擦肩而过。他总是把自己关在研究室里,学生跑去请教问题,他随便一句“看来没问题嘛”,就把他们打发走。有时他完全封闭自己,不论谁去敲门,哪怕是事先约好的,他也会大吼一声:“滚开!”
以上细节,恐怕都是真实的,因为张纯如写的是传记,不是小说,她经过扎扎实实的采访,所举的事例都出于当事者的回忆。但这样的细节,很难出自我们记者的笔下,不信你去翻看有关钱学森的报道,类似的描述,保证一句也没有。多年来,我们的思维已形成了一种定势,表现科学家、出类拔萃的大师,照例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循循善诱等等。千人一面,千篇一律,苍白得可怕,也枯燥得可怕。
大师就是大师,无一例外充满个性色彩。因此我说,张纯如笔下的钱学森,其实更加有血有肉,生气充盈,因而,也更加惹人喜爱。
(《今晚报》11.5 卞毓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