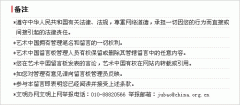徐皓峰:想在《武士会》中写出消失已久的社会结构
在长篇小说《武士会》“后记”中,作者徐皓峰忆及他学生时代在北京街头邂逅的两个老头及他们各自不可思议的言行,觉得“个人和历史是错乱的关系,人可能在任何时段都活过”,这当然只是有些感性的慨叹。不过,从做电影编剧、写小说再到当导演,他始终以独特的视角和个人风格强烈的表达方式努力贴近历史、虚构情节,以创作者姿态介入并左右不同年代人物的不同人生。“写着写着,突有身临其境之感,似乎活到别的时间里。下笔,不再是创造,而是入境。”他的这种自信几乎贯穿每部作品,电影如此,小说更加如此。“会有一种不讲理的自信,资料和推理都虚假,顺笔而出的,即是真实。”他在“后记”中说。
基本上,这些年来徐皓峰的写作在口述历史整理和长篇小说创作中交替进行。两年前那部纪实作品《大成若缺》问世后,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正在写新长篇──也就是新近出版的《武士会》。《武士会》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写起,主人公李尊吾身怀绝技而报国无门,历经十几年波折,深切体会到江湖险恶、人心莫测以及特定历史时期传统武术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价值判断乃至传播手段面临的巨大冲击后,最终创立中华武士会。书中通过对这个故事的讲述,对若干武人个性、遭际的描写,生动呈现清末政治斗争、社会生活和武林中人的境遇。
年初,徐皓峰参与编剧的《一代宗师》公映。无论王家卫在华语影坛的名头还是影迷们被吊了太久的胃口,乃至于主演中梁朝伟章子怡等大明星的号召力,这部电影的话题性和反馈热度都在意料之中。剧组奔走在各大城市的首映式上,徐皓峰责无旁贷担负起一遍遍和各路媒体、影迷解释片中种种玄机的重任,据他说从未这么忙过。当这波热潮渐落,回到北京的他终于有时间和本报记者边喝咖啡边说说新书《武士会》。
读书报:在《大成若缺》出版时你已动笔写《武士会》,后来还参与《一代宗师》编剧,这期间写长篇和剧本同时进行?
徐皓峰:给《一代宗师》做武术顾问之前就在构思《武士会》,写了开头,后来才做编剧。这三年可能是我迄今为止最忙的时候,王家卫拍《一代宗师》是拍拍停停,我的小说写作和编剧工作就交叉进行,这期间我还导了两部电影(记者注:《倭寇的踪迹》、《箭士柳白猿》)。
给自己导演的电影做后期的时候写《武士会》效率最高,做后期要面对剪接啊声效啊很多问题,常常一周都找不到思路。这时写小说好像去旅行,不是有很多作家写不出来就出去旅行或者去某个固定的地方活动活动么?我相当于用写小说的方式在工作间放松,这等于用另外一个创作的压力缓解做电影的压力。
读书报:和做编剧当导演比起来,写小说的个人创作成分更大?
徐皓峰:写《武士会》其实是完成我自己的历史诉求,实现我的知识体系的一种积累。之前写《道士下山》和《大日坛城》,动笔前我都做了采访,有非常鲜活有质感的口述,我在写作时的分寸感也基本离这些讲述不太远。但这两部长篇的写作有点像文人画的感觉,胸中有丘壑,兴之所至、信笔由来。
从前我写武侠只要完成一个臆想的写作就行,这个意象可能从真实里来,也可能是真实的水影,从水珠里折射世界,无限丰富、光彩淋漓。是半梦半醒的分寸感,写生活中的传奇。而写《武士会》,我想要把一种已经消失了的社会结构写出来,对自己的要求是不要给人臆想,要给人一个现实。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写作的感性成分开始下降,理性开始增长,有现实的需要。
读书报:能具体说说“已经消失了的社会结构”吗?
徐皓峰:最近在读木心的《文学回忆录》,木心在其中特别说到民间的高贵跟可爱。他说哪怕一个普通的手艺人,没什么文化,也还是有他的高贵和尊严。他老是跟陈丹青他们感慨,说你们都没经历过我家乡的那种民间。我小时候生活在北京,或多或少能体会到木心所说的这种东西。
木心书里讲的这种民间的高贵,也就是一种社会结构。说得再深一点,是从明朝末年开始形成的。当时的社会各阶层虽然在经济上不平等,但在审美倾向上却基本一致。从晚明到清再到民国,甚至包括我小时候的20世纪80年代,那种北京胡同里有文化的老人,就算身份上有高低贵贱,但他们的审美标准差不多。
读书报:《武士会》中涉及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乃至武林规矩、江湖道义都有据可查,在写作中你怎么从搜集的资料出发拿捏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分寸感?
徐皓峰:写历史因素这么重的小说,最关键的是打破历史常识和定见,关注一些新资料,这些资料对历史可能是重新的解释。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找到一个解释历史的方式——一旦涉及到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我会放弃文学虚构,由史料逻辑代替文学逻辑往前推。文学是有概括性的,可能在局部上放弃了真实,但在概括层面上又获得了真实。具体到《武士会》,有时面对具体的历史环节,就决定不用人物原名,比如写到有个关刀王五,原型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刀王五。但是有些人物,比如慈禧、张之洞、袁世凯,小说中的事件是跟历史重合的,就用原名。
读书报:从《道士下山》到《大日坛城》再到《武士会》,你的几部长篇小说年代背景都是清末民初,你好像对这个年代情有独钟?
徐皓峰:我小时候住在姥姥家,会听老人讲一些家族中清末民初的事情。我看到的第一本有文字的书,是姥爷带着我读的绣像本《儿女英雄传》。人如果关注现实,就一定也会关注历史,会思考现实种种从何而来。这种想法一追就会回溯几百年,人们生活的惯性巨大,几十年几百年都往往会重复很多同样的东西,回过头去一找,就找到几百年前。而我是从晚清中寻找对现实种种疑惑的答案。
读书报:《武士会》中戏份最多的要算充满英雄陌路意味的李尊吾,其他很多人物要么身心缺失,比如大太监崔希贵,要么个性极端,比如李的师弟沈方壶和李的几位弟子,这是当时武林中人的常态吗?
徐皓峰:从正史中读到的魏晋人物和《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民间的口述历史、历代迭传的历史中有个规律,出格的人和事更容易流传下来。所以我写这些人物,其实就是写人之偏。
读书报:与你之前的小说相比,《武士会》中儿女情长比重加大,对李尊吾和仇家姐妹感情关系的设计令人唏嘘,这么写有何深意?
徐皓峰:这么写肯定是有想法的,我用了大量篇幅来铺垫这个想法。李尊吾对仇家姐妹的感情,长相守,未能得,有点像我们这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感情,觉得近在身边,但是得不到。念念不忘,没有回响。哈哈。
在中国传统特别是自晚明开始的文学和绘画中,女人和太阳月亮一样,是种巨大的想象,以此来表达什么事情都可以。我的电影《箭士柳白猿》中也是这样。有人问我,片子里有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个被玷污的姐姐,你对这个角色是怎么想的?我说,这个被玷污的姐姐就是传统的中国。对方说,哦导演是不是你做影评出身,对自己的影片过度解读了?我们怎么看不到这种痕迹?其实这就是文学的创作方法。对中国人来说,男女关系很多时候就是社会关系、人与历史关系的比喻。
读书报:中国武术自古以来都强调师徒传承、门派意识强烈,但《武士会》的最后却实现了拳术普传,这是特定年代下的一种无奈吧?
徐皓峰:确实是无奈之举。历史上,中国文化每次普传都会引发大规模的堕落,因为普传违反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结构。中国民间结构是复合型的生态结构,各阶层的审美和礼仪标准大体一致,但从事的事情不一样。比方说,士大夫阶层创作书画,农民也可以欣赏,而民间有民间的艺术,手工艺啊说书啊。不同阶层的艺术,大家可以相互理解,但创作上界限分明。好多士大夫也会去听说书,而一个农民如果家里能挂一幅名家的画,也是巨大的喜悦。
为什么说每次普传都带来文化衰落?因为打破和超越了不同文化所属的创造者阶层,让传统文化被不具备原创力的阶层来创作就是破坏。当然,推动文化普传的人有报国之心,不可否认的是,历史上拳术普传也确实有其积极意义。这种文化普传延续到现在,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新文人画”潮流,虽然其中也有大家,但仍然是一场艺术灾难。当时很多画家50岁前受的都是苏联教育,没过过一天传统文人的日子,去画新文人画就带来很大的拧巴,最后变成大家玩廉价的笔墨技巧,情趣跟真正的传统文人不沾边。
从前的中国是“宗师制”国度。特别是艺术和技术行业,靠服众,让大家在道德和专业水准上服气,不靠暴力、集权和垄断,这才是宗师。这样的好处是能维护着艺术、技能的高端水准不至于堕落下去。普传毕竟是历史大变迁中的选择,其实是应急。当社会结构被破坏,社会趋向扁平化,大家都差不多,就不太重视术业有专攻这回事了,就出现普传,但传的只是一时之技。《武士会》里写的普传就是时代变迁和个人情感变迁后的自然变化。关于普传的话题超出这本书的容量了,或者那是另一本书要写的。
《武士会》后半部分在写怎么建立武士会的过程,也在写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如何不断崩塌的。建立一个东西的时候,同时一定有很多大楼在倒塌。你看《茶馆》,第一幕里的中国是礼乐之邦,大家讲规矩讲情义有礼数,到后来就是礼的丧失,中国人完全成了耍蛮无礼、没有规矩的民族。
读书报:说说你和王家卫的合作吧,怎么从武术顾问又到编剧?
徐皓峰:王家卫是我在上大学时就很感兴趣的导演,和他合作更多出于个人原因。《逝去的武林》让我在武术界出了名,王家卫在筹拍《一代宗师》过程中邀请了一些武术家去剧组畅谈或是搜集素材,他希望我能以武术顾问身份加入到剧组,帮着接待武术界人士,这样剧组也感觉有里有面。我不愿意做武术顾问,那等于要借用我的武术人的身份。教我拳的李仲轩先生不让我和武术界的人交往,于是我跟王家卫说,任何武林人士到剧组来,都替我找个借口避开。所以有些武林人士虽然知道我,但第一次见到我也还是在这部电影首映式上。唯一的例外是叶问的徒弟、教梁朝伟拳法的梁绍鸿先生,没办法,我不懂咏春拳,写剧本的时候要向他请教。
读书报:你的小说时常会穿插些宗教、哲学内容,《一代宗师》里说习武之人有三个阶段: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你觉得你的小说、电影创作目前达到哪个阶段了?
徐皓峰:这是道家的概念。我想我现在是见众生的阶段,见自己和见天地是说人从自己这儿、从天地那儿获得灵慧,这相对容易一些。但见众生是最难的。
读书报:你怎么看中国的武侠文化?
徐皓峰:从文化角度来讲,武侠文化反映了当时的市民文化。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莎士比亚戏剧和巴尔扎克小说?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的小说和戏剧大多满足于谈奇说怪的消费,并不是要对社会结构、人物内心深层次情感有所触及和体现,在出发点上就和西方文学不同。谈奇说怪没那么多精神诉求,结尾也常常是大团圆。
这种传统在民国时期的老武侠小说和香港的武侠电影那里表现得更加充分。除了金庸等几个武侠小说大家的作品有一定的人文价值和文学因素,其他大部分武侠作品也仍是在谈奇说怪。
读书报:《一代宗师》公映了,《武士会》也出版了,今年是不是可以放松一些?
徐皓峰:2013年,我想多写几个中短篇,有六七年没怎么写中短篇了。写中短篇是我写长篇和拍电影之外的闲笔,是一种写作技巧上手工艺的满足。今年也有电影计划,所以写中篇的另一个好处是改编成电影的便利──我的两部电影都是改编自我自己的中篇小说。
至于写作题材上,还是会写武林,我很好奇,想看看写武林最终能写到什么程度,能走多远。作家的题材像老天给男人安排的女人一样,是避不开的。(本报记者 丁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