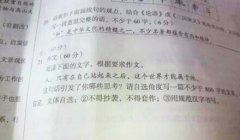“我们的中国梦”文艺作品征集专版
爱你胜过爱自己(散文)——写给所有残疾人的中国梦
张岩
如果不是把你伪装起来,我知道普天下人都会看到我的残疾。我不愿让别人看到,不愿让一个“废”字轻易地把我的心刺穿。亲爱的,请原谅我伪装了你。因为你的与众不同,我一直以来的自卑心理让我不愿将你示众。我当然惭愧。尽管我把你伪装得温温暖暖的,让你跟随着我,无声无息,一动不动。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委屈,是不是怨我。我相信你是委屈的,因为委曲求全啊。其实我也想把你放出来,让你在冬日的阳光下,晒晒暖暖的太阳,让你跟我一起行走在大庭广众中间,自由地摆动,潇洒地挥舞。可是我怕别人笑你。怕别人说你影响市容,有碍观瞻。我没有勇气把你展示出来,我只能在一个人的夜里,在乳白色的日光灯下,把你赤裸在我的眼前,让你见见星光,见见这个叫“人类”的世界,让你看着我,让我看看你,让我看你时在心里向你忏悔。我知道我把你伪装,其实是在伪装我自己。我相信你也是知道的,你因为知道而不会笑我。亲爱的,请原谅我的自卑和自私。
打从娘胎里出来,你就跟着我,不离不弃,默默无声,跟了我四十多年,跟到现在。我对你的最初记忆是这样的:那时,我大约六岁吧,我和我的哥哥在阳光底下玩黄豆,我的穿着蓝碎花褂子的年轻而美丽的母亲坐在我们身边纳鞋底。母亲不经意间看出了我和哥哥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左手。我的哥哥两只手玩耍黄豆,而我只用右手玩耍,左手低垂在一边不动。我于是在母亲的怀抱里开始了我求医的行程,也开始了我的眼泪多于欢笑的童年。我记得我来到人世间的第一次哭是因为举手。那天,哥哥举右手说:毛主席万岁!我学着哥哥的样子,也举右手说毛主席万岁。哥哥又举左手说毛主席万岁,我再举左手时,却举不起来了。我用了好大的劲,我的左臂却纹丝不动。我急得哭了。我抓了哥哥的脸,而后我又抓了母亲的脸。那年我七岁。七岁那年我明白了一件事,我的左手跟别的孩子左手不一样,别的孩子左手都能跟右手一起玩游戏,我不能,我只能站在一旁看别的孩子玩游戏。
我哭的时候,你是否也为我难受?你无声无息的,垂挂在我的左边,以不争的事实,成了我有别于别的孩子的残疾的左臂,也成了我淡白人生中不能更改的胎记甚或是烙印。
你知道吗?我哭的时候,我母亲也是哭的,她是偷偷哭的,在不让我看到的地方哭。后来我母亲就不哭了,总是把我揽在怀里,在灯下抚摩你,看你。为我洗澡的时候,先为你洗澡,为我剪右手指甲的时候,先把你的指甲剪了。再后来,母亲驮着我,从村里到镇里到县里再到市里到省里,为你治病,母亲这一驮就驮了三年。母亲说你的病好了,我的病也就好了,她的病根也就去了。可是终未治好你的病。母亲问医生,没有希望了吗?医生说,没有。母亲又问,真的没有希望了吗?医生还是两个字,没有。母亲一下子泪流满面。
医生说,你患了小儿麻痹后遗症。你肌肉萎缩了,你比右臂又瘦又小,不好看。我面对你时,无声无息;就像你面对我时,无声无息。我把你隐藏起来,隐藏在袖管里,除了我和母亲,我不会轻易地让别人看到你。就是从那时起,我学会了伪装。伪装你,伪装我自己。
你一直跟着我,跟着我走进了学堂。你知道吗?走进学堂的一刹那,面对几十双星星样眼睛,我的脸多红啊。我怕他们看到你,从而取笑我。“怕”是什么滋味?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在我幼小而稚嫩的心里,就战战兢兢地领略了。因为你,我怕上体育课。同学们到操场上去了,我却躲在教室里,把窗户和门都关上。后来有一次,我还是被校长发现了。我没有勇气出卖你,我只说我感冒了。第二天,全校师生大会,校长就点名批评了我,并把我叫到台上亮相。众目睽睽,我像被扒光了衣服,羞得无地自容。后来是怎样散会的,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带着你,躲在厕所里哭了一场。那时我念初二了,我有了自尊。
因为你的丑,我受了伤害。很长时间里,我怨你、恨你,我把你藏得更隐蔽一些,更安全一些,我讨厌你,我不想再见到你,我害怕见到你,可是那次在家里洗澡,在衣服脱光了之后,我还是与你有了不可回避的面对面。看着你,我震惊而且沮丧。你那么软弱无力地存在着,在我眼里多么陌生啊。你是谁的?为什么跟着我?那一刻,我甚至有了自残的念头,我想,如果有一把刀,我会拿起刀把你砍下来,扔得远远的。我恨你,你却不动声色,还是那么死心塌地地跟着我,我看你看到后来,心里就湿了。我用我的右手为你洗澡时,眼泪就落下来。人生不能没有左膀右臂,你再丑,也是我的左膀啊。
上初三时,因为你,我又有了麻烦,其实还不止于麻烦,你甚至把我的前程和命运都改写了。毕业前夕,我爱上了一个叫“玫”的女孩,因为你,我有了自卑,我爱她却不敢向她表白,当我最终还是鼓足勇气把一纸简短的情书放进她课本的最后一页时,我发现她和另一个男生在月光下的小树林里有了约会。
后来就是中考。紧接着就是毕业。她中考考得不错,远走高飞了;我因为你的存在,中专体检没有过关,我回家了。
我呆在家里,无所事事。茶不思,饭不想,整天躺在床上睡大觉。母亲不声不响,只顾着做她的饭,炒她的菜,从我床边走过时,没有一点声音,像一小股风,旋即来了,旋即又走了。我偶尔看母亲一眼,发现母亲弯着腰走路,那脚轻飘飘的,像不沾地似的。母亲端着饭碗进来,劝我起来吃饭,我假装睡觉,不理母亲。母亲唤着我的小名,唤着劝着,劝到后来,我竟来了脾气,我说不要你管!母亲端着碗愣在那里,愣成了一尊雕像。
傍晚时分,我去了荷花塘。荷花塘在村南,不远。我坐在塘边,看荷花,看荷叶,看荷叶下面的小鱼摇头摆尾游来游去。小鱼儿多自由啊,我觉得我也是一尾小鱼,只是现在搁浅了,我要走进塘里,沉到水里和小鱼儿一起畅游。似乎还留恋点什么,我慢慢地转过头,就看到不远处的榆树底下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立在榆树后面,向我这边看,袖口在脸上擦来抹去。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我去了城市,母亲留在家里。
你改变了我人生的路径,你让我不得不离开土地,不得不离开母亲,去了没有母亲的城市。
让我说你什么好呢?是感激?还是怨恨?你之于我,是幸还是不幸?
在城里谋生,我依然时刻把你带着,因为你是我的左膀,我要用我的右臂养活你。或者说,是你带着我,以一种默然的不屈的精神牵引着我,让我在这广大而陌生的世界里勇敢地谋生。
然而,请你原谅,亲爱的,卑微的我还是没有勇气把你放开。你让我自负的同时,也让我自卑,让我坚韧的同时,也让我孤独。你早已在我心里筑了一道墙,我无法逾越,也不敢走进墙外边的那个凡俗的粗陋的世界。
我还要伪装你,伪装我自己。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还你以公道?什么时候才能扒去套在我身上的伪装?
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把你伪装得很好,却还是因为你,我一次又一次地出丑。那次,在火车上,坐在我身旁的几个女孩玩手机,玩到后来,一个女孩尖叫起来,说她的手机丢了。那女孩翻遍自己身上所有的口袋,也没有找到。于是几个女孩一齐把目光向我投来,我成了她们眼中的贼。我原本老老实实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的,与她们并无瓜葛,现在却因她们的逼视,我脸红心跳,如坐针毡。那丢手机的女孩说,你看到我手机没有?我说,没有。女孩说,对不起,请你配合一下,把你的左手拿出来。我说,不行!几个女孩几乎是同声说,拿出来!我还是没有勇气把无辜的你展示给她们看,那一双双眼睛都像刀子。我面红耳赤,和她们争吵起来。后来乘警来了,在他要求下,我不得不把你从口袋里抽出来,送到那么多健全人的面前。羞愧让我紧闭了眼睛。再后来,乘警解了围,乘警要那女孩拨丢失的手机号,那女孩拨了,所谓丢失的手机在挂在窗前的一个小包里响起来。我睁开眼,把凶狠的目光投给了那女孩。我真想打她一耳光。可是我忍住了。能怨她吗?也许我要是早些说出我左臂残疾,就不会有这尴尬事啊。也许该打的是我自己。我去了洗手间,在那里,我又为你穿上伪装,然后,我抽了一支烟。
这是刚进城的事了,后来我在这城里开了书店,靠卖书写字养活我自己,养活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妻子。我认识了一个文友,她的散文写得很好,一直是我仰慕的。一次饭局,我们见面了,她送了我一本刚刚出版的散文集,她为我签了名,并面带微笑站起来,以谦逊的姿态,双手把书捧给我,我却只能用右手来接。我深感惭愧的同时,并在心里深感歉意,接她的书时,我说谢谢,把腰弯下去,算对我的歉意向她鞠了一躬。她当然不知道我是在向她鞠躬,那时,她还不知道我身有残疾,她肯定生气了,肯定怨我太不懂礼貌了。我第二天想给她发个短信,解释一下,打开手机,找她的号码,却一不小心,把她的号码删除了。这没有解释成的事,放在心里,放久了就成了心事,到现在它还盘桓在我的心头,无法释怀。后来她知道了我的身体情况,想来已原谅我了吧?
因为你的负累,我的脆弱的心不仅自卑,而且敏感。很多在常人司空见惯的小事情,之于我,都会敏感起来,有时甚至是过敏。那是一次编辑老师和文友的聚会,说笑间,我们谈到领导和座位的关系,一个文友就和我开玩笑,说我是领导,应该上座。“领导”一词,在任何人听来,都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名词,没有任何指向性,而在于我,听了就觉得格外刺耳。我的过敏的思索告诉我,这位文友羞辱了我。因为我不是领导,而只有“一把手”才是领导啊。他是笑我肢残啊。我很伤心。聚会结束后,我给编辑老师打了电话,向他诉说了这个事,说到后来,我委屈地哭了。编辑老师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他像哥哥,和我们这帮文友相处得很好。他在电话里向我保证,那个文友所说的“领导”绝没有取笑我的意思,那个文友爱开玩笑,性格很好,完全可以把他当朋友相处。我听了老师的话,后来我和那个文友相处了,真的处成了好朋友。一次饭局,这个朋友跟我讲了,他说他听编辑老师说了,他说:“我说那话绝对没有别的意思,你爱信不信!”我们碰杯了,因真诚和激动,杯子被碰碎了。
我知道,因为你,我对于“手”字太敏感了。因为你,我离群索居;因为你,我的老师又把我引进一个健康而美好的文学圈子里,扶着我在健全人的世界里走近了一步。亲爱的,我是该谢你,还是怨你?你之于我,是幸还是不幸?是上苍安排你来激励我并辅佐我的人生吗?
我和你像患难与共的兄弟,又像相濡以沫的夫妻,相互支撑,不离不弃,在这城里打拼了十五年。十五年,说短暂也短暂,说漫长很漫长。然而,我和你,你和我,我们毕竟走过来了。
带着你,我回了一趟老家。老家老了,老家的母亲也老了。那个穿着蓝碎花褂子的年轻而美丽的母亲没有了,现在,我的母亲老成了外婆。我为母亲洗了头发,又为母亲洗了脚。我为母亲剪了手指甲,又为母亲剪了脚趾甲。母亲拿过剪子,把我的左手拿到她的怀跟前,为我剪起了指甲。我想起了小时候,我的指甲都是母亲剪的,她心疼我残疾的左手,总是先剪左手的指甲,然后再剪右手。我看着母亲戴着老花镜为我剪指甲的样子,心里暖暖的,也酸酸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满满盈盈的,就滴了下来。泪光里,我又看到母亲驮着我四处求医的背影;看到母亲立在大榆树的后面偷偷地用袖子抹泪。
母亲为我剪完了指甲,问我,这些年,你在城里,指甲是谁帮你剪的?我说我自己剪的,我会剪指甲了。我当然没有告诉母亲,我右手的指甲有时是用嘴啃的,有时是放在砖墙上磨的,有时是用脚趾压着指甲刀再剪去手指甲。
夜里,躺在妻子的身边,妻子把我的左臂抱在怀里,就哭了。我记得恋爱那会儿,第一次跟妻子见面时,妻子也是哭的。那是一个没有月光的晚上,妻子要看我的左手,我说不行,你要看我就把右手给你。因为妻子是个健全人,面对她,我有自卑感。妻子还坚持要看,我就放了我的左手,给了她。她两手抚摩着我的左手,眼睛看着我的脸,后来她就哭了。她说这么好的一个人,老天爷为什么这样对你?!她在我怀里哭了好久,又说,你不要太难过,残疾又不是你的错。
再后来呢,纯朴、善良的她,就做了我的妻子。她在老家照顾我的母亲,为我生儿育女,我在城里为我最爱的亲人苦苦打拼。
我在家乡小镇上的澡堂里洗了澡。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家乡的澡堂里洗澡。之前,我每一次洗澡,都是在家里烧水洗的。因为我怕,我怕你——我的残疾的左臂被人瞧见。现在,我想我不怕了。因为母亲和妻子都给了我最大的鼓励。母亲说,你到澡堂里洗个澡吧。你怕什么?
是啊,我怕什么?我为什么要怕?为了母亲,为了妻子,为了给了我幸与不幸的左臂,我想我该走出来了。走出心里的阴影,走进充满阳光的世界。
在澡堂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脱光了衣服,终于,套在我身上四十多年的伪装被我扒得一干二净。让大家看看我吧,看看我健全的右臂和残疾的左臂吧。我向澡池走去,许多人都在看我,其实,他们并没有笑我。
他们并没有笑我,也许这世界本来就很健全,也许这四十年,我活在自己为自己构筑的有缺陷的小世界里,自己笑自己吧?
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热水澡。我把我的左臂洗了,把我的心洗了,把我的灵魂洗了,我想,明天,面对我的人生,我就可以轻装上阵了。
我要感谢你,我亲爱的残疾的左臂,你自始至终陪着我,让我体验到了比常人多得多的人生滋味。当幸与不幸向我迎面走来时,我哭过,笑过;当幸与不幸在我背后走远,它们又成了我的财富。
我当然还要感谢我的亲人,感谢我的朋友,当幸与不幸来临时,是他们或她们给了我全部的爱。是爱让我坚强,让我冷静地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我还要感谢生活,感谢命运,是它们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行,因此,我的时光没有虚度。
谢谢你,亲爱的,我会永远爱你,胜过爱我自己。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残疾朋友。
此文已于2013年第十一期《北京文学》发表。2014年第二期《读者》转载。
作者简介:张岩,男,肢残,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主创散文和小说,在省市级报刊发表散文近百篇,2012年在大型文学杂志《清明》发表中篇小说两部。
手机:16552656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