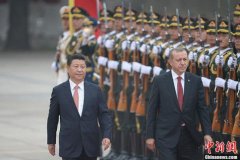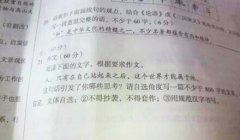琦君散文 散淡着乡愁与思亲的“土作品”
6月8日是作家琦君逝世纪念日。
在台湾女作家中,琦君以古典文学根基深厚而闻名,也被视为台湾散文大家。
琦君的文字并不华丽,却被誉为华语文坛最温暖的一支笔。出身名门,也历经家族变故,1949年赴台后更是遍尝艰辛,这一切却不能令琦君的文笔变得有一丁点儿的尖刻,她总是温柔地讲述苦难,在平淡中蕴藏深情,正是那些毫不雕饰、如口语般亲切的字句,无数次令人热泪盈眶,感动又酸楚。
她写得最好最多的,是怀乡思亲的散文。白先勇曾将琦君与另一位台湾作家林海音相提并论:“林海音写活了老北京的《城南旧事》,而琦君笔下的杭州,也处处洋溢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琦君也留下很多关于母亲的散文,诚如白先勇所言,“琦君最感人的作品,都与母亲有关。”
琦君总是谦称,我这个是“土作品”。对于这些“土作品”的写作缘起,琦君曾在《烟愁》后记中这样说:“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
故乡的桂花雨
选自《桂花雨》,尔雅出版社 1976年版,有删节
中秋节前后,就是故乡的桂花季节。
一提到桂花,那股子香味就仿佛闻到了。桂花有两种,月月开的称“木樨”,花朵较细小,呈淡黄色,台湾好像也有,我曾在走过人家围墙外时闻到这股香味,一闻到就会引起乡愁。另一种称“金桂”,只有秋天才开,花朵较大,呈金黄色。
小时候,我对无论什么花,都不懂得欣赏。尽管父亲指指点点地告诉我,这是“凌霄花”,这是“叮咚花”,这是“木碧花”……我除了记些名称外,最喜欢的还是“桂花”。桂花树不像梅花那么有姿态,笨笨拙拙的,不开花时,只是满树茂密的叶子,即使开花季节,也得从绿叶丛里仔细找细花。它不与繁花斗艳。其香气味,真是迷人。迷人的原因,是它不但可以闻,还可以吃。桂花,真叫我魂牵梦萦。
故乡是近海县份,八月正是台风季节。母亲称之为“风水忌”。桂花一开放,母亲就开始担心了:“可别做风水啊!”她担心的,一是将收成的稻谷;二是将收成的桂花。
桂花也像桃梅李果,也有收成呢。母亲每天都要在前后院子走一遭,嘴里念着:“只要不做风水,我可以收几大箩。送一斗给胡宅老爷爷,一斗给毛宅二婶婆,他们两家糕饼做得多。”
桂花开得最茂盛时,不说香闻十里,至少左右十几家邻居,没有不浸在桂花香里的。桂花成熟时,就应当“摇”,摇下来的桂花,朵朵完整、新鲜。如任它开过谢落在泥土里,尤其是被风雨吹落,那就湿漉漉的,香味差太多了。
“摇桂花”对于我是件大事,所以老是盯着母亲问:“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呢?” 母亲说:“还早呢,没开足,摇不下来的。” 可是母亲一看天空阴云密布,云脚长毛,就知道要“做风水”了,赶紧吩咐长工提前“摇桂花”,这下,我可乐了,帮着在桂花树下铺篾簟,抱桂花树使劲地摇,桂花纷纷落下来,落得满头满身,我就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啊!”
母亲洗净双手,撮一撮桂花放在水晶盘中,送到佛堂供佛。父亲点上檀香,炉烟袅袅,两种香混和在一起,佛堂就像神仙世界。
桂花摇落以后,全家动员,拣去小枝小叶,铺开在簟子里,晒上好几天太阳,晒干了,收在铁罐子里,和在茶叶中泡茶,做桂花卤,过年时做糕饼。全年,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香中。
中学时到了杭州,杭州有一处名胜满觉珑,一座小小山坞,全是桂花,花开时那才是香闻十里。我们秋季远足,一定去满觉珑赏桂花。“赏花”是借口,主要的是饱餐“桂花栗子羹”。因满觉珑除桂花以外,还有栗子。花季栗子正成熟,软软的新剥栗子,和着西湖白莲藕粉一起煮,面上撒几朵桂花,那股子雅淡清香是无论如何没有字眼形容的。
我们边走边摇,桂花飘落如雨,地上不见泥土,铺满桂花,踩在花上软绵绵的。这大概就是母亲说的“金沙铺地,西方极乐世界”吧。母亲一生辛劳,无怨无忧,因为她心中有一个金沙铺地、玻璃琉璃的西方极乐世界。 于是我也想起了在故乡童年时代的“摇花乐”,和那阵阵的桂花雨。
西湖忆旧
选自《琦君散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有删节
我生长在杭州,也曾在苏州住过短短一段时期。两处都被称为天堂,可是一样天堂,两般情味。这也许因为“钱塘苏小是乡亲”,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它格外有一份亲切之感。平心而论,杭州风物,确胜苏州。住杭州则心灵有多种感受。古寺名塔似遗世独立的高人逸士,引人发思古幽情。何况秋月春花,四时风光无限,湖山有幸,灵秀独钟。可惜我当时年少春衫薄,把天堂中岁月,等闲过了。莫说旧游似梦,怕的是年事渐长,灵心迟钝,连梦都将梦不到了。因此我要从既清晰亦朦胧的梦境中,追忆点滴往事,以为来日的印证。若他年重回西湖,是否还认得白发故人呢?
我的家在旗下营一条闹中取静的街道上。这条路全长不及三公里,被一条浣纱溪隔为两段。过小溪行数百步便是湖滨公园。入夜灯火辉煌,行人如织。先父卜居于此,就为了可以朝夕饱览湖光山色之胜。父亲不谙钓鱼之术,却极爱钓鱼。春日的傍晚,尤其是微雨天,他就带我打着伞,提着小木桶,走向湖滨,垂下钓线,然后点起一支烟,慢慢儿喷着,望着水面微微牵动的浮沉子而笑。他说钓鱼不是为了要获得鱼,只是享受那一份耐心等待中的快乐。
夏夜,由断桥上了垂柳桃花相间的白公堤,缓步行去,就到了平潮秋月。凭着栏杆,可以享受清凉的湖水湖风,可以远眺西湖对岸的黄昏灯火市。临湖水阁中名贤的楹联墨迹,琳琅满目。记得彭玉麟的一副是“凭栏看云影波光,最好是红蓼花疏,白公秋老;把酒对琼楼玉宇,莫辜负天心月老,水面风寒。”令人吟诵回环。白公堤的尽头即苏公堤,两堤成斜斜的丁字形,把西湖隔成里外二湖。两条堤就似两条通向神仙世界的长桥。唐朝的白居易和宋朝的苏东坡,两位大诗翁为湖山留下如此美迹,真叫后人感谢不尽。外西湖平波似镜,三潭印月成品字形的三座小宝,伸出水面。夜间在塔中点上灯,灯光从圆洞中透出,映在水面。塔影波光,加上蓝天明月的倒影,真不知这个世界有多少个月亮。
六月十八是荷花生日,湖上放起荷花灯,杭州人名之谓“落夜湖”。这一晚,船价大涨,无论谁都乐于被巧笑倩兮的船娘“刨”一次“黄瓜儿”。十八夜的月亮虽已不太圆,却显得分外明亮。湖面上朵朵粉红色的荷花灯,随着摇荡的碧波,漂浮在摇荡的风荷之间,红绿相间。把小小船儿摇进荷叶丛中,头顶上绿云微动,清香的湖风轻柔地吹拂着面颊。耳中听远处笙歌,抬眼望天空的淡月疏星。此时,你真不知道自己是在天上还是人间。如果是无月无灯的夜晚,十里宽的湖面,郁沉沉的,便有一片烟水苍茫之感。
髻
选自《红纱灯》,台湾三民出版社1969年版,有删节
母亲年轻的时候,一把青丝梳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白天盘成了一个螺丝似的尖髻儿,高高地翘起在后脑,晚上就放下来挂在背后。我睡觉时挨着母亲的肩膀,手指头绕着她的长发梢玩儿,双妹牌生发油的香气混着油垢味直熏我的鼻子。有点儿难闻,却有一份母亲陪伴着我的安全感,我就呼呼地睡着了。
每年的七月初七,母亲才痛快地洗一次头。乡下人的规矩,平常日子可不能洗头。如洗了头,脏水流到阴间,阎王要把它储存起来,等你死以后去喝,只有七月初七洗的头,脏水才流向东海。所以一到七月七,女人都要有大半天散发。有的女人披着头发美得跟葡萄仙子一样,有的却像丑八怪。母亲乌油油的柔发像一匹缎子似的垂在肩头,微风吹来,一绺绺的短发不时拂着她白嫩的面颊。她眯起眼睛,用手背拢一下,一会儿又飘过来了。她是近视眼,眯缝眼儿的时候格外俏丽。我心里在想,如果爸爸在家,看见妈妈这一头乌亮的好发,一定会上街买一对亮晶晶的水钻发夹给她。妈妈一定是戴上了一会儿就不好意思地摘下来。那么这一对水钻夹子,不久就会变成我扮新娘的“头面”了。
父亲不久回来了,没有买水钻发夹,却带回一位姨娘。她的皮肤好细好白,一头如云的柔鬓比母亲的还要乌,还要亮。
两鬓像蝉翼似的遮住一半耳朵,梳向后面,挽一个大大的司髻,像大蝙蝠扑盖着她后半个头。 全家搬到杭州以后,母亲不必忙厨房,而且许多时候,父亲要她出来招呼客人,她那尖尖的螺丝髻儿实在不像样,所以父亲一定要她改梳式样。母亲就请张伯母给她梳了鲍鱼头。那时,鲍鱼头是老太太梳的,母亲才过三十岁,却要打扮成老太太,姨娘看了只是抿嘴笑,父亲就直皱眉头。我悄悄地问她:“妈,你为什么不也梳个横爱司髻,戴上姨娘送你的翡翠耳环呢?”母亲沉着脸说:“你妈是乡下人,哪儿配梳那种摩登的头,戴那讲究的耳环呢?”
母亲不能常常麻烦张伯母,自己梳出来的鲍鱼头紧绷绷的,跟原先的螺丝髻相差有限,别说父亲,连我看了都不顺眼。
从那以后,我就垫着矮凳替母亲梳头,梳那最简单的鲍鱼头。我点起脚尖,从镜子里望着母亲。她的脸容已不像在乡下厨房里忙来忙去时那么丰润亮丽了,她的眼睛停在镜子里,望着自己出神,不再是眯缝眼儿的笑了。我手中捏着母亲的头发,一绺绺地梳理,可是我已懂得,一把小小黄杨木梳,再也理不清母亲心中的愁绪。因为在走廊的那一边,不时飘来父亲和姨娘琅琅的笑语声。
我长大出外读书以后,寒暑假回家,偶然给母亲梳头,头发捏在手心,总觉得愈来愈少。想起幼年时,每年七月初七看母亲乌亮的柔发飘在两肩,她脸上快乐的神情,心里不禁一阵阵酸楚。母亲见我回来,愁苦的脸上却不时展开笑容。无论如何,母女相依的时光总是最最幸福的。
名家简介>>
琦君 1917年出生,当代女作家。原名潘希真。浙江永嘉人。14岁就读于教会中学,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师从词学家夏承焘。1949年赴台湾,在司法部门工作了26年,并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后定居美国。
琦君出版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30余种,包括《烟愁》、《细纱灯》(获中山文艺创作奖)、《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读书与生活》、《千里怀人月在峰》、《与我同车》、《留予他年说梦痕》、《琦君寄小读者》、《琴心》、《菁姐》、《七月的哀伤》以及《琦君自选集》等。她是著名电视剧《橘子红了》的作者。
本版图片 据网络
以上内容来自:城市晚报
[责任编辑:yfs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