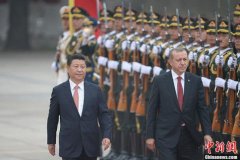我读季羡林散文
初读季羡林先生的散文是在1956年。那时,我正在先师王瑶教授的指导下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开设每周四学时、为期一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那是特别强调“文学史一条龙”的年代,而今而后,现代文学史恐怕都不再有如此重头的分量了。我当时还真有一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日以继夜,遍查各种旧期刊杂志,当然是为了上课,但潜意识里也难免还有那么一点好胜之心,想在王瑶老师那本已是包罗万象的《新文学史稿》之外,再发掘出一批文学珍宝。我以为季先生早期的散文就是我重新发现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情的民族,抒情诗从来是我国文学的主流。虽然历代都不乏道学先生对此说三道四,如说什么“有情,恶也”,“以性禁情”之类,但却始终不能改变我国文学传统之以情为核心。最近从郭店竹简中读到,原来孔孟圣人的时代,就有人强调:“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又说:“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可见情的传统在我国是如何之根深叶茂!我以为季先生散文的永恒价值,就在于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这一个“情”字。
但是,只有真情还不一定能将这真情传递于人,古人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形于言”才是真情是否能传递于人的关键。而“情景相触”构成意境,又是成功地“形于言”的关键之关键。在季先生90年代的作品中,《二月兰》是我最喜欢的一篇。二月兰是一种常见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间,花形和颜色都没有什么特异之处。然而,每到春天,和风一吹拂,校园内,眼光所到处就无处不有二月兰在。这时,“只要有孔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去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如果就这样写二月兰,美则美矣,但无非也只是一幅美“景”,先生的散文远不止此,随即把我们带到“当年老祖(先生的婶母,多年和先生同住)还活着的时候”:每到二月兰花开,她往往拿一把小铲,到成片的二月兰旁青草丛里去挖荠菜,“只要看到她的身影在二月兰的紫雾里晃动,我就知道在午餐或晚餐的餐桌上必然弥漫着荠菜馄饨的清香”。先生唯一的爱女婉如活着时,每次回家,只要二月兰正在开花,她也总是“穿过左手是二月兰的紫雾,右手是湖畔垂柳的绿烟,匆匆忙忙走去,把我的目光一直带到湖对岸的拐弯处。”而“我的小猫虎子和咪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往往在二月兰丛里看到她们:一黑一白,在紫色中格外显眼”。1993年这一年,先生失去了两位最挚爱、最亲近的家人,连那两只受尽宠爱的小猫也遵循自然规律离开了人间。“老祖和婉如的死,把我的心都带走了。虎子和咪咪我也忆念难忘。如今,天地虽宽,阳光虽照样普照,我却感到无边的寂寥和凄凉。回忆这些往事,如云如烟,原来是近在眼前,如今却如蓬莱灵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午静携侣寻野菜,黄昏抱猫向夕阳,当时只道是寻常”,这些确实寻常的场景,当它随风而逝,永不再来时,在回忆中,是何等使人心碎啊!当我们即将走完自己的一生,回首往事,浮现于我们眼前的,往往并不是那些所谓最辉煌的时刻,而是那些最平凡而又最亲切的瞬间!先生以他心内深邃的哲理,为我们开启了作为审美客体的二月兰所蕴含的、从来不为人知的崭新的世界。
如果说展现真情、真思于情景相触之中,创造出令人难忘,发人深思的艺术境界是先生散文的主要内在特色;那么,这些内在特色又如何通过文学唯一的手段——语言得到完美的表现?我以为最突出之点,就是先生自己所说的:“形式似散,经营惨淡”。所谓“散”,就是漫谈身边琐事,泛论人情世局,随手拈来,什么都可以写;所谓“似散”,就是并非“真散”,而是“写重大事件而不觉其重,状身边琐事而不觉其轻”。
要作到这样的“形散而实不散”实非易事,首先表现在结构上。先生的每一篇散文,几乎都有自己独具匠心的结构。特别是一些回环往复、令人难忘的晶莹玲珑的短小篇章,其结构总是让人想起一支奏鸣曲,一揆咏叹调,那主旋律几经扩展和润饰,反复出现,余音袅袅。先生最美的写景文章之一《富春江上》就是如此。那“江水平阔,浩渺如海;隔岸青螺数点,微痕一抹,出没于烟雨迷蒙中”,就像一段如歌的旋律在我们心中缭绕。无论是从吴越鏖战引发的有关人世变幻的慨叹,还是回想诗僧苏曼殊“春雨楼头尺八萧,何时归看浙江潮”的吟咏;无论是与黄山的比美,还是回忆过去在瑞士群山中“山川信美非吾土”的落寞之感的描述,都一一回到这富春江上“青螺数点,微痕一抹,出没于烟雨迷蒙中”的主旋律。直到最后告别这奇山异水时,还是:“惟见青螺数点,微痕一抹,出没于烟雨迷蒙中”,兀自留下这已呈现了千百年的美景面对宇宙的永恒。这篇散文以“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的诗句开头,引入平阔的江面和隔岸的青山。这开头确是十分切题而又富于启发性,有广阔的发展余地,一直联系到后来的吴越鏖战,苏曼珠的浙江潮,江畔的鹳山,严子陵的钓台。几乎文章的每一部分都与这江水、这隔岸的远山相照应,始终是“复杂中见统一,跌宕中见均衡”。
除了结构的讲究,先生散文的语言特色是十分重视在淳朴恬淡,天然本色中追求繁富绚丽的美。在先生笔下,燕园的美实在令人心醉。“凌晨,在熹微的阳光中,初升的太阳在长满黄叶的银杏树顶上抹上了一缕淡红”(《春归燕园》)。暮春三月,办公楼两旁的翠柏“浑身碧绿,扑人眉宇,仿佛是从地心深处涌出来的两股青色的力量。喷薄腾越,顶端直刺蔚蓝色的晴空。”两棵西府海棠“枝干繁茂,绿叶葳蕤”,“正开着满树繁花,已经绽开的花朵呈粉红色,没有绽开的骨朵呈鲜红色,粉红与鲜红,纷纭交错,宛如天半的粉红色彩云”(《怀念西府海棠》)。还有那曾经笑傲于未名湖幽径的古藤萝,从下面无端被人砍断,“藤萝初绽出来的一些淡紫的成串的花朵,还在绿叶丛中微笑……不久就会微笑不下去,连痛哭也没有地方了”(《幽径悲剧》)。这些描写绝无辞藻堆砌,用词自然天成,却呈现出如此丰富的色彩之美!
先生写散文,苦心经营的,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文章的音乐性。先生遣辞造句,十分注重节奏和韵律,句式参差错落,纷繁中有统一,总是波涛起伏,曲折幽隐。在《八十述怀》中,先生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这些十分流畅、一气呵成的四字句非常讲究对仗的工整和音调的平仄合辙,因此读起来铿锵有力,既顺口又悦耳,使人不能不想起那些从小背诵的古代散文名篇;紧接着,先生又用了最后四句非常“现代白话”的句式,四句排比并列,强调了节奏和复沓,与前面的典雅整齐恰好构成鲜明的对比。这些都是作者惨淡经营的苦心,不仔细阅读是不易体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