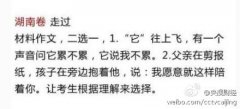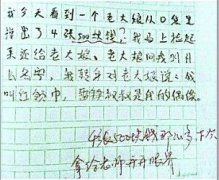故乡的小河
西北的城隅,流淌着一条小河,河面流水潺潺,岸边翠柳依依。傍晚的时候,我常常携了妻子,牵着女儿,踩着散落在石板道上的艳丽夕阳,任柳丝拂过脸庞,漫步向远方。
许是对小河怀有更深厚的情感吧?每当徜徉在这条小道上,置身于这份少有的宁静中,我常常会放慢脚步,与妻子女儿拉开一段距离,一个人凝视着波光粼粼的河水,眺望着对岸郁郁葱葱的湿地,倾听远处传来的虫鸣蛙鼓。有时,也独自踱到水边,蹲下身来,捧一捧清凉的河水,举到眼前,再任其从指缝间沥沥流落,看着河面被击起的层层波纹,我的心中也会荡起片片涟漪……
有一次,妻子似乎看出我的心思:“又在想念家乡的那条小河了吧?”
这句话,一下子拨动了我失落的心弦,发出一串串酸楚的音符。而一旁的女儿正叠了几只小纸船,放在河面上,转过小脸对我说:“爸爸,爸爸,你可以坐着我的小船回家了。”
“哦——”
看着那几只悠悠远去的小纸船,我的眼眶湿润了,心,也跟着湿润了……何止今天?又何止此时?我曾无数次地用这绵绵的乡愁叠起这样的一只只小船,企图载着我的思念,与河水顺流而下,绕过绵绵群山,穿过重重迷雾,驶入我故乡的河湾,驶回我远去的童年……
我无法忘记家乡前面那条清澈的河湾,河湾旁边那丛深的蒿草甸,更无法忘记生活在河湾旁边的村人们,还有村人们讲述的关于河湾的那些美丽传……
家乡的小河,由后山里几条帘子一样的小溪汇聚而成,汨汨地绕过断崖脚边,流经村口的河床,涌入村前的河湾。童年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她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字,是识字以后,才知道小河的名字居然标注在地图上,虽然不长,却弯曲迂回,如妇人做针线遗下的一根线头儿。不过,村人们谁也不肯遵从书本上的那个称谓,认为那是官家的名称,并不代表自己和祖先们的意愿,而一直称她为“仙女河”。
为什么称它“仙女河”呢?这里边还有一段祖先们传下来的故事:远古的时候,这里只有草木繁生的山岭洼地,并没有什么河流,只是有一天,天宫的仙女们下凡观赏人间美景,云游至此。恰逢骄阳似火,酷暑难当,仙女们个个颜面汗浸,粉脂斑驳,欲寻个湖泊沐浴,结果寻遍附近也没有结果。其中一个美貌仙女急中生智,飞上断崖,将手中的绢带一扬,飘落到草地上,瞬间就变成了一条河流,流淌出清凉凉的河水。仙女们饮水解渴,沐浴畅游,直到消暑之后才去别处游赏。后来,人们就将这条河定名为“仙女河”,一辈一辈传续至今。
听着这个古老的传说,如在听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谁也不去轻信它,而从老人讲述的表情里,我们又不难看出那是一棵怎样虔诚的心啊!是怎样的一种自豪啊!无不是在叹服和景仰仙女们的点化神功,又在庆幸自己有生能陪伴这条神来之河!为了河水的洁净,与这个故事很老很老的,还有一些不成文的规矩:不准往河水里泼脏水,丢脏东西,就连小孩子撒尿也不许,否则,脏污了河水,会激怒仙女,触犯天条,要遭受报应的。村里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都在一心恪守着。
清晨,我们带着未散的梦境,揉着惺忪的睡眼,隔窗望去,眼前偌大的河湾里,清澈透碧,波平如镜。东山巅染着灿烂朝霞,清清楚楚地倒映在河中央,水,一下就被山染绿了,山,也一下就被水润活了。那时候,我们望着眼前的这幅景象,常常会生出许多遐想:“是山跳入了河中,水才绿了?”“不是,是水罩住了山,山才活了。”大人们这样打趣地回答。偶有一只小船远远划来,山立刻被剪刀似的裁成了一段段的碎片,缓缓浮游向岸边,小船驶远,那悠悠的河水又将山在欲合欲断中缝合完整,经这一剪一合,我们的梦也就醒了。
每天,我们如泥鳅一般从大人的腿缝间钻出,一路奔跑过那条踩压瓷实的田埂,一头扎进清凉凉的河水里。村里的孩子一般长到五、六岁时,就由大人领着,先是在浅滩练游水,逐渐由浅入深,之后再练潜水。等我们的身子晒得黑黝黝的,水性也就可以让大人放心了,所以我们都会水,而且水性并非一般能比。做个旱鸭子,是要被同伴耻笑和歧视的,就连大人们也要把这当作一件稀奇事,挂在嘴边上传来说去。伙伴们相聚一起,时常会互不服气地争吵一番,而唯一平息的办法就是大家一同憋足了气,一个猛子扎进水下,忽然间,河面上就没了一丝的动静,过了好半天,说不定谁在河中央的哪里钻出个小脑瓜,两手在头上捋一把,扭头寻找着同伴,自豪地向对方招着手笑。
河湾的旁边,是一片平展开阔的湿地,我们习惯称它“蒿草甸”。每年春初,听到河湾里“喀嚓”“喀嚓”跑过冰排,河水开始漫延出来,将小草和野蒿滋润出绿色。随后是燕子飞回来了,小鸟兴奋地叫起来了,在虫儿的歌唱声中,蒿草一天一天地长高,葱翠茂密,人没走进去没几步,就淹没在那绿帐之中了。我们在水里玩腻了,就钻进蒿草里,或在矮浅处扑蜻蜓,逮蝈蝈,或在丛深处“捉迷藏”,“抓蛇头”,玩得热闹喧天,酣畅淋漓。直到日傍西山,家家房顶炊烟袅袅,似在招呼我们“回家喽——”“吃饭喽——”,我们才感觉到肚子已是瘪瘪的,个个水鸭子一般回到村里。
小河是富有而无私的,水里的鱼虾似乎永远也打不完捞不尽。农闲的时候,村人们三两个搭成一伙,带上鱼具,驾着小船,在碧波之中荡来漾去。驾船的,抛网的,摘网的,忙个不停。小船在欢快的笑声中驶到岸边,卸下来的有鲤鱼、黏鱼、鲫鱼、泥鳅……红艳的、黄绿的、青黑的,品种繁多,颜色搀杂。而人们只将大鱼装在柳筐里,担回家去,小一点的却要撒回河里,因为在每个人心里,还有一条规矩不能违,要想靠这条河养活,做事就不能绝尽。
那些夏末秋初的日子里,是收虾的最佳时机。晚饭后的空闲,人们不肯歇息,手持网竿沿着浅水滩的草稞趟过一段,便是沉甸甸的半网虾,棵棵硕大肥实,活蹦乱跳的。女人们连夜用清水洗了,放在铁锅里煮熟,第二天一早,院子里铺开一张席,将炒熟的虾凉晒在上面,站在村后的断崖上放眼望去,家家的院子里红彤彤一片,衬托着满园的葱翠,如忽然盛开的一畦畦芍药花。晒干以后收起,转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炒上一盘添在餐桌上,为清苦的日子点缀出丰盛。
还有那夏日的傍晚,劳作一天的人们,吃过晚饭,习惯地踩过田埂,来到河边的古柳下乘凉。古柳被几经漫延的河水冲刷,裸露出一条条苍虬的根脉,人们坐上面,望着眼前的河水和远处的青山,津津有味地谈古论今。夕阳撒在河面上,偶有轻风吹过,整个河面顷刻间波光潋滟,光彩绚丽,如一条巨大的鲤鱼身。茂密丛深的蒿草里虫鸣蛙鼓,此起彼伏,清脆悦耳。如此欢歌尽舞,如此激情高涨,难道这些另类生灵们在为疲惫的人们举办一场音乐盛会吗?在这不知不觉中,一身的疲劳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