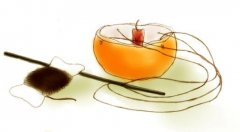过渡(散文)
过 渡(散文)
□湖南 鲁田
窗外已是叶落潇潇的秋,雨淅淅沥沥地走来,风也不时穿过房间,翻动一切可以细读的经典章节。这时,最适合在书脊的边缘独处。
临摩着何绍基的《大唐中兴颂》的帖子,内心涟漪起来,不长进的自责在周围的空气中荡漾开去。心中生起了无以名状的忧愁,于是,我放下笔砚,禅坐在我最衷情的围棋边,随着棋子的起起落落,我逐渐沉醉在清人的“当湖十局”中,忘忧于黑白子的精妙计算与力智搏击。这时,门,被猛然叩响了。起身时,我才想起已与友人相约同去拜访一位智慧的老友。
古风盈荡的老友并不老,只是他时常与古人神会的言谈举止让繁华喧嚣中的我们心仪不已。起始彼此居所相距颇近,少顷即至。老友室中悬有一幅龙狂蛇舞,细辩是一偈颂:“粉墨登场笙管浓,谁知槛外雪花重。推窗窥见清凉界,明月芦花不定踪。”令人心绪飞扬。联想老友,脑中竟然呈现出不“糊涂”的板桥影像。稍坐片刻,知己三人同往近处一小酒馆,沽得几两散酒逸兴便随着酒香流动着。文,侃得樯橹灰飞烟灭;武,推手之间道骨仙风;世人皆醒我独醉或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慨叹就在这种放旷之中步入逍遥境界。
酒馆踞闹市街脚,门面的开合仍依赖二十二张既长且厚的编号木板,门口老桂树的虬枝上一古拓的手书酒旗,门内有两张方方正正的油漆剥落的八仙桌。在这里,经典的风雅古意足以感伤怀旧,如果有雨,更显烟雨苍茫的雅致韵味。在这个现代大都市,这经风沐雨的带阁楼的木板房固守着江南古镇最后的一抹遗痕。
酒馆的主人姓肖,是孕育美人和猎艳传奇的山幽水秀的湘西人氏。老友与肖先生是在那年修大西南三线铁路时相识的。那年临近春节时,连队准备宰掉喂养了一年的肥猪做一顿丰盛的年饭,便派了老友去买砧板。老友在返回驻地时,天空落起了雨夹雪,两块磨盘大的杂木砧板上雪花愈积愈厚,雨水慢慢融浸下去,越来越重,最终把疲惫的老友压趴在雪地里。老友挣扎着往前蠕动,直到昏迷过去。聚缘天定,这时山中打柴的肖先生发现并搭救了老友,从此,笃定了两人的生死之谊。
推土机随着我断断续续了解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一步步在逼近小酒馆。老友那次从死亡中站起来后,心性巨变。“三线”连队中出名的打架斗殴大王从此消遁,老友开始珍视生命,用补贴甚至是衣服去换得一摞摞书本。书籍的力量使老友从狂热走向沉静,并焕发出生命质量的光泽。
这一片安谧的都市盲点的古老居民,最终被推土机的噪音一家家地驱散到了耸立的摩天巨厦。因征迁而推倒的老屋一点点的向天空敞开,蚕食一般渐渐地吞噬了路人经年的习惯和感觉。在工人们极不耐烦的催促中,我们最后离开那家厮守多年的酒馆,其时已只有空空的厅堂。我们每一次聚会的热烈讨论和意气风发的演武,曾引来众多的看客和酒友的喝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接连吟咏的默契犹在耳畔。所有的欢乐和书生意气被轰鸣而来的推土机彻底埋葬了。
当时,老友手中仍握着一只杯和杯中的酒,那一刻,他高声咏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樽还酹江月。”身边没有江,天上也没有月,老友还是将满杯的酒挥手洒入扬尘,随后头也没回,独自走了。黑色的风衣裹着老友渐行渐远,我却惊诧于那一刻我明显地感觉到空气中的桂花幽香和着浓烈的酒香异常地扑鼻。所有的心灵皆为老友气盖山兮的张狂所震慑,浮哗的人声隐遁了,只有马达的轰鸣在继续细细碾碎着老友的江南。精神田园沦陷后,我与老友的居所也被迅速攻占,江南被社会的文明与文明的文化演绎成了一堆没有个性、没有风格的钢筋和水泥的积木。丢失江南的我与老友都成了新圈地运动的弃儿。
不久,我终于放弃对抗,屈服在一套只剩有精神的商品房里。宝剑收敛,吉它喑哑。据悉老友搬到了城市的边缘,一个三面为殡仪馆的坟山包围的地方过渡,他一直谢绝我前往探望。
今日老酒馆中一友相约同往老友新居,我早已欣然答应。车至殡仪馆门口,问明去路,便沿山脚直插了进去。一排排、一列列的墓碑整齐寂然地掠过我的视线,目光所及,除了坟就是碑,我想我对秋天的况味有全新的认识了,人死后如此排列有序而又整齐划一,那么生呢?是不是有如水流是有规律可循的。看到静的,便想到动的,看见山,便想到水。世间原本是如此和谐的,然而,活着的人为什么又混乱无序,抑或只是人们看不清最后的序列而盲目地拥挤与插队……
“老友说,他是将军。我现在明白了!”友人向我问着话,打破了沉默,并用以削弱秋天在这特定环境中带来的萧瑟,甚至是恐惧。对,是有阅兵的味道。我看一眼那个个方阵,明白军人出身的老友是触景生情或……,或什么呢?与如此众多的亡灵比邻而居,不想恐惧就应该有勇气,且是大智慧的勇气。勇气往往因知耻、因追求平衡而生。而欲与死者平衡,对生者又意味着什么呢?心灵的电光火石相撞击,让我有了许多不可言传的领悟。
“怎么,浮想连翩了?小心被鬼摄去了三魂六魄。”不经意之间,我们已经到了山底,久未相见的老友鬼魅般站在面前。我似乎感觉到老友身上一股鬼气,我调侃他:“选了这么一个所在,你是想当捉鬼的钟馗,还是驭鬼的姜子牙啊?”老友冲我一笑,笑中的一丝赞许有鬼气氤氲,并久久萦绕不散。
老友的居所为化学危险品仓库的库房。原先的守卫因耐不住寂寞与恐惧都是稍作停留便匆匆离开了,薪水虽高,但仍无人敢于与鬼长久同住。还好,无房的老友暂避于此,恰好弥补了无人看守之虞。
我想老友藉此地修炼。从喧闹的尘世先期来到这个最后的归宿所在,领悟沉沦在红尘中的一些东西,老友显然已明了名利背后的不归路。言谈中表露出他对生与死、闹与静的种种心得映证了我的感觉。
一个渐渐清晰的故事不期浮出脑海:某寺庙中,晨起做功的小和尚问老和尚如何参禅,又怎么领悟佛法。老和尚不经意地拨落了青油灯芯上的灯花,片刻不语。室中顿时明亮了许多,小和尚望着油灯,又看看老和尚,不敢再问也不敢动。天刚放明,有一只苍蝇从门口飞向灯火,绕灯一匝后,却扑向蒙着白纸的窗户,但怎么也飞不出去,撞击着窗纸嗡嗡轰响。老和尚终于开口:找不到出路,又不知沿来路回去,如何得法。言毕,弹出一颗念珠,苍蝇边的窗户纸破了一个洞,苍蝇终于穿窗而出,小和尚也顿开茅塞叩谢而去。
我说毕,大家相视而笑。老友说:窗纸可以用许多方式捅破……那一刻,不知老友是忽略了灯花还是触动了潜藏意识而转移了话题。
这使我回想起彼此间的一段误会,在接触到的禅宗中,“会心一笑”与“当头棒喝”构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种顿悟模式。老友却善于用故事中老和尚的手法启开我们的智慧,我因此在某次顿悟后书了条幅“虚喝”呈送老友作谢,意指故事中有隙的空间可供渐悟。不意引发了老友的愤懑,然而,谁也不愿再去捅破这层窗纸,直至今日。
生命中,我们承受的困惑与苦难,从未只降临到别人身上,而不曾施于己身。但又有几人懂得去探究呢?一层薄薄的窗纸岂止苍蝇穿不透,人又面对过多少扇纸窗啊!此外,生命燃烧中出现的灯花,又有几人曾试图拂去以使生命亮丽呢?一定要等到油尽灯灭吗?
辞别老友返回时,望着那一层层、一排排整齐的墓碑想:老友自诩将军,是登临彼岸的心境使然。我呢?忽然又闻到了记忆中的一阵桂花飘香,但不是红尘喧嚣中的,是不是从生死的渡口飘来的呢?
如果我们不知道此岸与彼岸的距离,又如何渡得过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