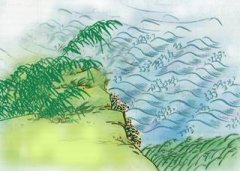外国诗歌汉译与现代格律诗
“五四”以来,中国的白话新诗在形式上一开始就是以突破一切格律束缚的自由诗面貌出现的。尽管从20年代起,有识之士就致力于新诗格律的探索,经过几代诗人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创作实践都已取得显著的成就,而且具有不断发展的态势。然而无庸讳言,对此远未引起必要的关注、应有的重视;就形式而言,整个诗坛几乎一直是自由诗占居统治地位。只有新月派盛行期间,她曾短暂地风光了一回。然而那时,她毕竟还处在“初级阶段”,致贻“豆腐干”之讥(对有些只讲每行字数相等而不顾其内在节奏规律的作品是触其痛处的)。
人们普遍认为,自由诗这种中国诗歌传统中前所未有,又与传统诗歌大相径庭的形式本是舶来品,脱胎自外国诗歌。如所公认,郭沫若的《女神》受惠特曼影响极大,宗白华、冰心为代表的小诗则与泰戈尔难脱干系(1)。这里且引用周作人《论小诗》中的一个论断以资佐证:“中国的新诗在各方面都受欧洲的影响,惟有小诗仿佛是在例外,因为它的来源是在东方的。”(2)诗的变革自有其诸多内在的原因,但是必须寻求形式上的突破口。对此,康白情作了具体的分析:“日本英格兰美利加底‘自由诗’输入中国,而中国的留洋学生也不免有些受了他们的感化......由惊喜而模仿,由模仿而创造。”(3)
毕竟懂外语、能读原著的人是少数,大多数爱好者接受外国诗歌影响还是通过译诗的途径,或通过中国自由诗受到间接影响。所以译诗的状况如何,就不能不对他们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去,对“五四”以来外国诗歌的传播,一般只看到积极的方面,很少提及其负面效应(极左思潮下的盲目排外不予考虑)。其实,这是远不全面的,妨碍了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
直至1982年,卞之琳先生才以其真知灼见捅破了这层纸,把这个问题挑明。他指出:“译诗,比诸外国诗原文,对一国的诗创作,影响更大,中外皆然。今日我国流行的自由诗,往往拖沓、松散,却不应归咎于借鉴了外国诗;在一定的‘功’以外,我们众多的外国诗译者,就此而论,也有一定的‘过’。”(4)这“过”就在于,将大量本来有着严密格律的原作,不顾其“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体”的特点,而简单地将其译为自由诗了事。这样,就在人们心目中造成普遍的误解,以为外国都是自由诗的天下,因而忽略了中国几千年诗歌的格律传统,认识不到创造中国新诗格律的必要,在客观上限制了格律体新诗的发展,甚至有些诗人、理论家还粗暴干预现代格律诗的研究与实践。何其芳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格律诗的主张,在上世纪50年代遭到大规模围剿,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一事件遗留的恶劣影响,贻害至今。
为什么卞老认为译诗艺术“成年”了呢?原来在1981年里,他先后读到屠岸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本、杨德豫译的《拜伦抒情诗七十首》和飞白的论文《译诗漫笔》(由此得知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属于格律诗,他已在努力通过翻译诗恢复其原貌),感到惊喜,觉得译诗艺术“好象一下子达到成年了”。实际上,这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五四”以来许多译者的共同探索的结果。这些译作的成功,有助于澄清“外国诗歌都是自由诗”的误解,从而有利于中国新诗格律的建设。而事实上,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包括卞老自己(他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印行的《英国诗选》译序中就明确陈述了自己的主张:“我认为现在首先应主要如实介绍西方诗,保持原来面貌,以供我们根据中国实际的正确借鉴。”),还有查良铮(穆旦)、钱春绮等,除致力于准确转达原作内容外,也一直执着地进行着忠实地再现原作形式的努力。
而从闻一多开始,朱湘、孙大雨、卞之琳、周煦良等诗坛杰出人物,更是有意识地把对外国格律诗形式的把握与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建设结合起来。何其芳晚年翻译海涅、维尔特的作品,也是为了这同一个目的。卞之琳先生在《何其芳晚年译诗》一文说:“他埋头从事海涅诗、维尔特诗的翻译工作......只是在译诗上试图实践他的格律主张而已。”(5)为进一步说明这些译家的意图,特别对尚未广为人知的周煦良先生的英国诗人霍思曼《西罗普郡少年》译本和译序(6)作一比较详尽的介绍。
霍思曼(1859-1936)是19世纪90年代崭露头角的与哈代、叶芝齐名的英国三大诗人之一,其作品不仅曾经风靡一时,而在20世纪上半叶仍然享有盛誉,已经成为英国诗歌宝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1896年出版的诗集《西罗普郡少年》则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周煦良先生在译序里谈到他的翻译动机:“我从中学时代起就喜欢新诗......总是写得不满意。后来懂得一些英诗格律,觉得我们新诗也需要一种格律。”他先后用自己的创作诗和翻译华滋华斯的短诗来做实验,结果都不满意。直到1937年,受当时《诗刊》主编戴望舒之约,翻译《西罗普郡少年》时,才“发现这的确是我进行新格律诗试验的最好素材......在格律的严格要求下,融进我的译诗,使新诗的语言和表现力丰富起来。”他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孙大雨和林庚关于现代格律诗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包括孙大雨的翻译经验,其中主要是由英诗的音步转化为汉诗的音组(即音尺,或顿)的划分,以及借鉴韵脚的使用方式。所以《西罗普郡少年》也是严格依照原诗格律进行翻译的成功范例,可以说是译诗艺术“成年”的又一个例证,不过该书出版于1983年,没有能够纳入卞之琳先生的视野,来不及写进那篇文章而已。但是,它接踵而至,却正好印证了卞先生的预期:“随新一年的来临,不久会有更多更大的喜讯。”
在卞之琳先生“成年”说提出整整20年后,黄杲忻严格按照原诗格律翻译的《美国抒情诗选》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他在《译者前言》中对卞之琳先生关于“翻译诗对我国新诗的发展功过参半”的观点(亦见《何其芳晚年译诗》一文)表示认同,与之遥相呼应。译者详尽阐述了自己奉行的译诗理念和美学原则:“如果翻译中要考虑原作的风格,有无格律这一点恐怕是个显著而又基本的界限......(格律诗人们)之所以不避艰难,接受某专种形式的束缚,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这种形式本身就具有审美价值,能够为他们的诗歌内容服务......因此,从尊重作者、忠于原作和对读者负责等角度出发,对于既是原诗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其音乐性重要标志的格律形式,我们应努力尽到如实传达的义务”,“除了力求译文忠实于原作、读来上口,还注意把原作的形式移植过来,至少也要把原诗是有严谨格律的这一点反映出来”。他对那些不尽职尽责的译者、置原作格律于不顾的翻译方式提出有力的责难:那样,“是否会给人造成错觉,以为外国诗都是不讲格律的自由诗?”遗憾的是,这样的错觉早已相当普遍地形成了,为害非浅。
黄杲昕还通过自己出色的卓有成效的工作,雄辩地证明了以英诗为其源头的美国诗歌,不仅一开始就承袭了格律诗的传统,而且经过两百余年的发展,时至今日,格律诗仍在美国诗坛占有重要地位。也许出乎许多人的想象,不但如布莱恩特、朗费罗、狄金森等早期名家都是格律诗人,“超验主义”创始人之一爱默生、象征主义大师爱伦.坡、意象主义始祖庞德,以及大名鼎鼎的弗罗斯特都是以写格律诗为主,就是众所周知的以写自由诗著称的惠特曼最负盛名、在美国家喻户晓的作品《哦,船长!我的船长!》也是一首严格的格律诗呢。此诗每节八行,一共三节,各节相应行顿数相等,三节节式完全相同。这里,不妨再引用钱春绮先生所译的被称为西方现代派诗歌鼻祖的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的《恶之花》的《译本序》中的一段话来与此呼应:“他的现代性,是他的诗歌内容,而不是形式,因为,他的诗歌形式,还是古典的,传统的。例如,集中有不少诗都是用十四行诗体的严谨格律写成的。”而屠岸先生也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译后记》中除肯定这一事实外,还指出:“十四行诗体的生命一直延续到现代。例如英国的奥登、奥地利的里尔克、法国的瓦雷里都用彼特拉克的变体写十四行诗。”一提现代派似乎就意味着诗行参差,不讲音韵,形式上绝对自由,这是多么可怕的误解啊!要改变误导造成的无知和无知造成的偏见,事实才是最有力量的。而坚持在译文中保留原诗格律的可敬的翻译家们,正好为我们提供了无庸质疑的事实,有力地击破了关于外国诗歌的误解与偏见,从而使人们有了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学习、借鉴的可能。他们所做的工作意义重大,功德无量。
黄杲昕精心翻译美国诗歌,不仅是为了向中国读者奉献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而且也要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照物”,可谓用心良苦。他注意到“在我国创作诗的形式上,一方面是限制极严的古体诗,另一方面则是在形式上几乎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由诗”,惟独缺乏以现代汉语为语言载体的新体格律诗;进而发现恰好外国诗歌的格律对于我们创建新诗格律体系极具“借鉴参考的价值”:“除了许多现成格式可供选用外(例如,即使是格律很严的十四行诗,也有不少的压韵方式),诗人还可按其需要,设计出配合其作品内容的格律形式,从而在格律多样化上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他在翻译中不仅重视格律的移植,而且充分利用汉语固有的音节文字的特点,“注意反映原作中的音步数与音节数,表现出整齐划一或变化有序的建筑美或图形”。他的意图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的译诗实践,向几成公理的诗的“抗译性”扔出了挑战的白手套。
黄杲昕上述关于中国新诗格律的设想,与我不谋而合,殊途同归。所以我读了《美国抒情诗选》及其前言,不能不将他视为同道,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多年来,我在研究与实践中默默地坚持闻一多先生开创的,几代诗人、学者翻译家共同拓宽的现代格律诗道路,虽然在几乎由自由诗独霸的诗坛显得十分孤独,我却无怨无悔,乐此不疲。1994年11月,我向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北京雅园诗会提交了论文《现代格律诗的无限可操作性》的提纲,得到了与会人士的首肯,这一观点写入了大会总结。1996年此文写成后寄请屠岸先生审阅,他在回信中作了充分的肯定,并谈到外国诗歌的翻译问题:“本来这个‘无限’早就是客观存在,这在外国(比如英美)是个司空见惯因而毫不为奇的现象。”中国的现代格律诗“借鉴外国经验,发挥自身潜能”,也就自然而然地“输入了”这个“无限可操作性”。而“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加以突出,就使人感到异长醒目”,并且有继续探讨的必要。他还指出,许多人写新诗不懂得“顿”的道理,只是压上韵脚,就以为是格律诗了。这也与那些不讲求“顿”的翻译家有关,是他们造成了不懂外语、只能通过译文接受外国诗歌的读者的误解。这与卞之琳先生的“功过参半”论实质上毫无区别,不过表述有别而已(7)
在关于“无限可操作性”的论文中,我这样勾勒了现代格律诗的形式框架:“现代格律诗的两大类型,一曰‘整齐式’,一曰‘对称式’。简言之,前者就是在一首诗中,每行顿数相等的格律形式,后者就是在一首诗中,第一节每行顿数不等,可是以后每节相应行顿数相等的规律形式。”其体式的无限可能性体现在:整齐式因其每行顿数、每节行数和压韵方式的变化,可以衍生出许多种体式,至于对称式更可因首节(可以称之为“基准诗节”)“面目”的千变万化而体现其样式的无限丰富性。这也就是说,闻一多先生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提出的“相体裁衣”的主张完全是切实可行的。相信明眼的读者一定可以发现,我这里所说的整齐式与对称式,与黄先生所谓“整齐划一或变有序”实质上完全一致,而他所说的“在格律多样化上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与我的“无限可操作性”提法也是貌似神合,其义一也。此外,我还提出,经过实践的检验、汰选,还有望形成类似绝句、律诗的诸如四行、八行、十四行等固定诗体,它们也可以再分为整齐式与对称式。(8)。
不妨指出,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格律诗在理论上渐趋成熟的同时,其创作成果也取得了相应的收获。早在1986年,邹绛先生编选的《中国现代格律诗选(1919-1984)》就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各种样式的现代格律诗300余首,其中包括了“五四”以来几乎所有重要诗人的作品,许多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也有不少当代的佳作。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充分显示了许多格律诗的创作实绩和艺术活力。另一方面,十四行诗的“汉化”移植也成效显著,先后由国家级出版社印行过两本不同的相当翔实的选本。江苏学者许霆、鲁德俊还出版了35万字的专著《十四行诗在中国》,系统研究了这一西洋诗体在中国“落户”的现象(9)。
由此看来,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先行者和后继者们的确是从外国诗歌格律汲取了营养,又结合汉语自身的特点加以创造,已经总结出一套比较系统的可操作的方法。一方面通过外国格律诗形式的对应翻译,一方面通过创作实践来进行试验,经过几代诗人,包括认真对待原作格律的翻译家的努力,适合中国现代汉语特点的新体格律诗的创建已经取得明显的成绩,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可悲的是,在一向由自由诗占居统治地位的中国诗坛,一些无知、短视的诗人和理论家却闭目塞听,无视以至抹杀这一事实。这就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新诗的正常、健康的发展。这里可以举出一个典型事例来说明这种“无视”严重到了何种程度:上世纪80年代初,在重庆举行的一次诗歌座谈会上,笔者提出了诗歌的形式问题,求教于在座的诸多名家。一位德高望重的诗坛耆宿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是新诗不存在形式问题,每一首自由诗都有自己的形式。既无知又霸道,简直匪夷所思!将新诗与自由诗完全等同起来的情况也是在各种场合屡见不鲜,甚至在一些学术论文中堂而皇之地出现。这种对于常识的缺乏令人慨叹。
早在1954年,何其芳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适合它的现代语言规律的格律诗,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健全的现象,偏枯的现象”。要真正克服何其芳指出的自由诗一统天下的“偏枯”现象,使现代格律诗真正确立起来,实现这一目标还任重而道远,需要期以时日。正因为如此,就需要诗歌界的有识之士、有志之士为此付出不计成败的甚至带几分悲壮色彩的艰巨努力。毫不夸张地说,这的确是事关中国诗歌前途的大事,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注释:
(1)孙玉石《新诗流派发展的历史启示》,载《中国现代诗论》(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2)周作人《论小诗》,载《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新诗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3)康白情《新诗底我见》,亦见《中国现代诗论》。(4)卞之琳《译诗艺术的成年》(载北京《读书》杂志1982.3)。(5)卞之琳《何其芳晚年译诗》,载《何其芳诗全编.附录》(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6)《西罗普郡少年》由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7)此信经屠岸先生同意,载入万龙生《诗路之思》(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8)万龙生《现代格律诗的无限可操作性》,载《诗路之思》。(9)许霆、鲁德俊《十四行诗在中国》,苏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10)何其芳《关于现代格律诗》,载《何其芳选集》第二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