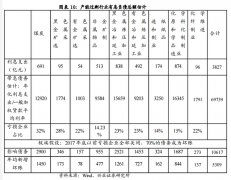评致龄诗集《莫若当初》
这是一本有着强烈辨识度的诗集,不只是因为作者以一个苗家人的身份,生活在遥远的南疆,却几十年对维吾尔族文化进行忘情歌唱,更重要的是这本诗集以独特的文学体例,于当下浩繁的诗歌作品中,呈现出别样的属性。
十二木卡姆,维吾尔族一种综合的艺术表现形式,集歌、舞、乐、诗、戏于一体,其中的诗歌形式双行诗叫做“格则勒”。一直以来格则勒的写作均以表现炽烈的情感为主题,通过纯真自由的诗句,赞颂边疆丰富热烈的生活,以及人们心中对美的热爱与歌唱。诗人致龄,仿佛南疆大地上的游吟诗人,他写的“格则勒”也是如此,奔放自由,恣意随性。其作品虽在说着爱情,但事实上更是诗人对自己生活的整个南疆大地、自己第二故乡的深情热爱。有爱才有美,才有对美的体验,才有生命与灵魂的自由。正如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说过的,“我相信美学的选择,是一个人高度的选择,一个人对美的体验越成熟,他的心灵就会更广泛,道德观念会更加的超群和集中,精神也会更加丰富与自由。”
土地养育肉身,文化养育精神。南疆大地的浑厚壮美,民族文化的深远神秘,给了诗人足够浓烈的美的体验,足够成熟的艺术审美力量。在这里,诗人的生命与灵魂皆有如再生一般,生长出有别于自己既有精神质地的纷繁经验。因此,诗人对南疆大地的天地风物满怀敬意与感恩,并展开前世今生般的挚烈审视与颂唱。如此结构出的边塞风情诗,深沉绚艳,炽真苍茫,仿佛是自我的心神交锋,仿佛是时空交错时的某种异样和解。
作者歌颂南疆大地上的自然万物、民族风情、文化习俗,以及炽烈如焰火的情感与生活。有一些诗句则表达对民族经典文化的热爱、敬畏,对经典的深情回望与重温。诗人以浑厚的情愫、深沉的敬意,忘情颂赞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父亲问我什么是柯尔克孜的光荣/阿依曲莱克一样美丽的白色天鹅/……我是您望穿双眼的千年征夫赛麦台/您是我白天鹅般美丽的阿依曲莱克”。诗句仿佛是从经典传说、民族文化中撷取而来的圣美珍珠,从史诗出发,又刻意与史诗保持神秘的距离。这种对想象力的大胆释放,同时亦令诗歌具有了叙事的风格、民谣般的旋律,亦增益了诗歌的底蕴、趣味。
诗人从自己鲜活的个人经验中获取诗意的可能,并在其中融入了更具深意的文化意识。在诗歌中抒写着有关灵魂的遗忘与记忆、有关天地的热烈与悲凉,从而抵达一种陌生的美。这份陌生中满含的是经典之气蕴,当一个诗人对一个民族的文明之旅展开刻骨的观想,便等同于建立了一种真切诚挚的美学诉求,个体的生命亦获得了宏大的精神在场。
“相思如果以昆仑为尺/谁有勇气读出两颗心的距离”。(《昆仑为尺》)无数的假设,便是无数的希冀与承诺,诗人面对南疆大地上的山谷峰峦、草原河流,以诗为琴,以情为乐,以爱为歌,彻夜不休地吟唱,仿佛唱了百千年。歌声在帕米尔高原升起,在昆仑山的梦里游荡。写给爱,念苦恨,都是浸在泪水中的甜;写给天地、河流山谷,写给奔涌而过的时间与空间,亦写给绽放的岁月划痕与风暴。诗句时而裹挟着浩荡的漠风,时而如月下金色的胡杨林一般辽远深阔:“我的须眉已被瀚海染白/这黄沙与尘土中皓首向东的翘望/若我可以把自己伫立成一棵树/也是一棵仆倒在地依然昂首的胡杨。”(《依然等你在老地方》)
“从来不敢辜负这一片雪域/所以我遥远的爱才如许深沉”。(《遥想的幸福叫喀喇昆仑》)这些诗句多与爱相关,其间深藏着一个远行人对故土的眷恋,而回归故乡后遗落在他乡的心魂,更有着同样的切切牵挂。离别思重,愁绪伤怀,茫茫南疆之间的孤寂与遥想,有如笛声在月下,九曲十折,百转柔肠。
在时间的驱使下,当更多的人在被动中放弃选择,成为一枚惯性的陀螺,诗人则于生活中顽强地表明自己的精神立场。不断迁徙中的诗人,在行走的脚步中发现生活中的诗意。他执拗而认真地将整个身心匍匐在南疆大地之上,倾听那片浑厚野性的沃土上缤纷阔远的音律——南疆大地上的羌笛如梦,西域月色中的昆仑万里,帕米尔高原的长箫寂寞,夏日雪域的壮美风物,今生来世的爱与相思。
致龄双行诗的意义,不仅在于复现出古老的“格则勒”的经典意蕴,更重要的是传达了一个现代诗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入探索,并于一种虔敬自由的写作中,揭示出一种全新而迷人的艺术秩序,那就是文学创作中古典与现代的艺术互文性。此间的古典与现代,成为彼此的秘密、佐证与延续,或者成为彼此的核心。一切既有的或规定的价值与准则,有了重新的指向,正是在这样重新的指向中,古典与现代在互文中共同焕发出新的生机。这样的作品必将夹杂着一种“复魅”的高贵,高贵得有如诗人诗句中弥漫的那些梦境、月光、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