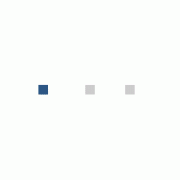从《乐府诗集》到现代民谣

![]()
木心说:“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过去我很信奉这句话,固执地认为尽管当下高楼林立、交通网纵横交错,人与人的距离只在一个按键之间,然而现代生活如此转瞬即逝,如此拥挤不堪,相反过去的悠然岁月熠熠闪光,过去总是无条件高于现在。然而当我回溯两千多年的《乐府诗集》,我发现,过去与现在,有一些微妙的存在,是共通的。
![]()
作为管理宫廷音乐的乐府机构,秦及初汉已经出现,但规模有限。至汉武帝,以重定郊祀之礼为契机,扩充其规模,丰富其职能,乐府遂成为即掌管朝廷郊祀乐,也包容民间新俗乐的重要礼乐官署。这些原本很可能消散在历史长河中的民间曲辞也因此得以传承至今。乐府诗以无声的文字诉诸视觉,以有声的吟唱诉诸听觉,诗与声即宫、商、角、徽、羽五音相调谐而成的旋律相合而形成统一体。如今,我们只能够看到《乐府诗集》文学层面上的艺术价值,至于这些曲辞旋律如何,已经散佚在历史长河中,今人无从知晓,只能通过文字的韵律加以想象了。
![]()
礼乐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主流地位。在古代的音乐文化中,以礼乐为代表的文化脉络被人们延续下来,并在新的社会结构中不断沿着两条途狂开始发展:一条是推行于上层,为官方政治利盜服务的礼乐制度;一条是流散于民间,为民众现实生活服务的礼乐风俗。
![]()
《乐府诗集》中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这些为宗庙祭祀、歌功颂德、鼓舞士气的服务于上层的曲辞被排在首位。这些歌曲文学性上相对较低,却依然在编排上被给予优厚,政治是一道无法避免的阴影,总会散落在各个角落。而当今的社会此类的歌曲依然经久不衰,尽管这些歌曲在民众中毫无传唱度,依然在各式国家形象大片中被大书特书。好在,历史总是公正的,这些文字尽管被安置在如此重要显眼的位置,它生命力的缺失使他所得到的关注是那么有限,能引起普遍共鸣的依然是那些民间情感普遍流露的结晶。
《乐府诗集》中更具有价值的是民间曲辞,而民间曲辞,无论古还是今,都是普遍存在的。民间曲辞对于当时的百姓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通过这些曲辞,他们抒发了自己的爱恨,揭示了社会的冷暖,传递了朴素而亘古的人生哲学。而民间,从来是不缺乏音乐的。民谣是一个亘古常新的社会文化现象,现代也有民谣歌曲,尽管受西方音乐的影响现代民谣的乐器转为吉他而非传统鼓吹横吹乐器,人们仍然借由旋律和歌词来表达着喜怒哀乐。
![]()
我喜欢听民谣,更喜欢看民谣。在我看来,民谣的歌词比谱子更重要,一首旋律再动听的歌,词差了总觉得丧失了味道,就如同咖喱饭里只有饭一样。同样的,尽管乐府诗谱不存,令人扼腕,但词留传下来了,便也足以令人欣慰。
采入乐府中的民歌一般要符合两条重要的原则:一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二是“可观风俗,知薄厚”。这两条相辅相成的原则积淀了古老而浓厚的礼乐思想,使得乐府民歌不仅将个人情感抒发淋漓,也传递了关怀社会与现实人生的艺术精神,也形成了浑朴天成的统一风格。而这两点,现代民谣也同样契合。我们看广为流传的《上邪》:
![]()
陈粒的《奇妙能力歌》里的“我看过沙漠下暴雨/ 看过大海亲吻鲨鱼/ 看过黄昏追逐黎明/ 没看过你”和《上邪》不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吗?《上邪》里铺排引起强调,引之为爱情休绝的条件;《奇妙能力歌》里铺排而接对比,对比从未见过的“你”。两种铺排皆为深情,一者为相爱相守的誓言,一者为爱而不得的告白。而当爱情失意时,古今的回应也是那么相似。
![]()
![]()
我们看《有所思》:
![]()
而在李志的《天空之城》里,“爱情不过是生活的屁”与《有所思》有着一样的佯作决绝;也有“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 感觉着你忽明忽暗”、“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 想念着你越来越远”同样彻夜不眠的怀念与眷恋。
![]()
![]()
爱情是亘古不变的母题。今人与两千年前的古人都在不遗余力地赞颂爱,怕言语表达不出内心的炽热,怕修辞修饰不了眼底的流波;今人与两千年前的古人都在不约而同地失恋,只能借歌辞宣泄内心的郁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此之谓也。
《乐府诗集》中所收录的乐府民歌与现代民谣,都各自形象地绘出了社会风貌,领着听者走进民众的现实生活,使我们得以领略那个时代民众的思想感情,表现了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可观风俗,知薄厚”,此之谓也。《乐府诗集》中和现代民谣里都有雏鸟的比喻。“‘雉子,斑如此!之于雉粱。毋以俉翁孺,雉子!’/ 知得雉子高飞止,黄鹄飞,之以千里,旺可思!/ 雄来飞从雌,视子趋一雉。‘雉子!’车大驾马腾,被生送行所中。翱翔飞从王孙行。”
《雉子斑》中以叙述老雉对雉子丧命于人悲痛不已,“刺时也,上以爵禄诱士,士以贪利罹祸,进退皆不以礼,贤者思遁世远害也。”而在崔健的《红旗下的蛋》中,以蛋自比旨在讨论自我与时代的关系,试图质问时代,同时表达姿态。
![]()
“头突然出来/ 是多年的期待/ 挺胸抬头叫喊/ 是天生的遗传/ 心里当然明白/ 我们是谁的后代/ 无论行为好坏/ 内心还是清白/ 权力在空中飘荡/ 经常打在肩上/ 突然一个念头/ 不再跟着别人乱走/ 虽然身体还软/ 虽然只会叫喊。”“现实象个石头/ 精神象个蛋/ 石头虽然坚硬/ 可蛋才是生命。”雉子与蛋的比喻都是从当时社会的磐石缝隙中挣扎长出的幼草,虽然声音微不足道,看似都在以卵击石,然而诚如歌中所唱,“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对现实有回应有反思的作品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艺术,才能穿越岁月的侵蚀,代代生机。
![]()
其实不仅现代民谣同汉代的“乐府诗”在形式和内容上有如此多相似之处,每个时代的民众一直借由曲辞发声。在整个传承谱系中,民间曲辞一直没有缺位,诗三百、鼓子词、昆曲、信天游……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或讲述凄美而醒世的故事,或直抒淳朴而炽热的胸臆,存在于它们的时代,代表了它们的时代,也改变着它们的时代。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卷首所写那样“时代精神的火花在这里凝冻、积淀下来,传留和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意绪,经常使人一唱三叹,流连不已。我们在这里所要匆匆迈步走过的,便是这样一个美的历程。”“乐府诗”能够穿越千年岁月经久不衰,是因为人类几千年的精神内核亘古不变;而现代民谣能够在大众流行乐的裹挟下偏安一隅,是因为其中的无限可能。这大概便是民谣之妙。
特邀写手|俞闻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