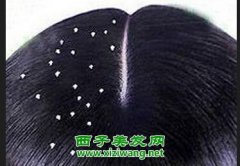第三代诗歌
在第三代诗人当中海子和骆一禾是游离于任何流派的孤独的抒写者,他们是大地乌托邦、乡村乌托邦的两个构筑者,他们是八十年代末期中国诗坛上两个真诚而富于激情的诗人,构筑鸿篇巨制是他们共同的诗歌追求。他们同为北京大学毕业的优秀的天才诗人。在短短的五年之中,海子写下了《太阳》、500首抒情诗和大量诗学笔记与论文,骆一禾则写下了长达8000行的长诗《世界的血》和《大海》,这使他们成为中国经典性作家。
海子(1964——1989),原名查海生,安徽省怀宁县人。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的一段慢速列车轨道卧轨自杀。海子生前留下大量诗稿和各种遗稿,后经其友人骆一禾、西川整理,先后刊于《十月》《人民文学》等杂志,并出版诗集《土地》《海子、骆一禾作品集》《海子诗全集》等多种,他的作品还多次被选入各种版本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年仅25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短暂的诗歌写作历程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精彩的诗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四姐妹》《亚洲铜》《黑夜的献诗》《春天,十个海子》等。海子自1984年创作完成了《阿尔的太阳》《亚洲铜》之后,便进入了一个诗情喷涌的爆发期,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他的抒情短诗。
渗透在海子的作品中的,主要是以浪漫主义为底色的生命意识和乡愁意识。他出身于乡村,对天空、自然、土地有一种特别本真和敏锐的感受,而这一感受一旦经过都市、历史剧变的催发,就很容易转向以“生命关怀”为中心的写作意识,尤其是诗人的精神期待不能落实、以至他发现在现代都市找不到精神世界的栖息之地时,那么死亡和以写作就易于彼此不分,变成一种腾跃于世俗人生和现实世界之上的一缕青烟,一种坦然弃绝于人世的终极价值认同。可以说,这是海子作品中反复出现“天空”“土地”“村庄”“麦子”“农妇”“孩子” “风”“夜”“月亮”“大海”等等指归性诗歌意象的潜在原因。
“麦子”是海子作品中反复咏叹的主题。海子在对“大地”的反复歌咏里追寻生存的本质和精神的故乡,将透明的智慧和纯净的梦想,植入泥土和麦子、河流和野花、粮食和马群这些乡村物象之上。海子书写了一片诗意的麦地、一个麦子的乌托邦(《五月的麦地》);海子在作品中热切地吟唱“天空”,从对土地“母体”的抒写转向对太阳这一“父本”的吟咏。体现海子纯粹、忧伤之外的另一面:热烈而疯狂(《四姐妹》);“死亡”是海子作品的另一个抒写母题。“麦子”在他的笔下由温暖变成痛苦:“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 痛苦的芒上”(《答复》),最后变成“绝望”:“抱着昨天的大雪,今天的雨水/明日的粮食与灰烬/这是绝望的麦子//请告诉四姐妹:这是绝望的麦子”(《四姐妹》)。海子没有像传统诗人那样沉醉于田园山水中,艰辛的个人乡村生活经验和中国农村贫穷苦难的历史与现实,以及从神启里既感受到水恒又悟出某种空洞,使海子承受了痛苦与绝望的体验。海子在“丰收”之中看到“荒凉”:“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上升”,“谷仓中太黑暗,太寂静,太丰收/也太荒凉,我在丰收中看到了阎王的眼睛”(《黑夜的献诗》);海子以自杀结束生命,再一次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诗歌主张。
美学原则
以1986年10月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为结体标志的“第三代”诗人在年龄经历上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大都是文革前后生人,以大学生、研究生和部分喜爱文学的青年工人为主,当他们进入成年真正面对社会的时候,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商品化了的时代。在小学中学受到的传统价值观念的教育,在新的商品经济规律面前似乎不堪一击,这个世界是缤纷的同时也是杂乱的,人们的灵魂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与诱惑。青年们本来不甚坚固的传统世界观开始崩塌,对以往所受到的教育包括书本上长辈们所传授的一切传统,他们都开始用怀疑的目光重新审视。于是,他们的诗歌中,传统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都不再处于被讴歌的主体地位,平民与平民的生活进入他们的视线,他们用平白如话的语言,将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与情感摆放在读者面前,并在其中表达着反崇高、反英雄、反理性、反文化的内容。这些诗,不论从其内容还是语言形式上,都与传统诗歌,包括前不久兴盛的朦胧诗大相径庭,于是不禁有许多人对他们的诗提出质疑,认为它们的格调不高,甚至已经脱离了诗歌乃至文学的范畴,而这种说法,正好又给第三代诗人的创作加上了一条新的本质性内涵,即“反诗”。
第三代诗人对平民的重视是有其社会历史背景的。八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国进入一个近乎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一个时期,此时,纷乱的生活使每个人惶惶不安但又都有着模糊的崇景,机会开始增多,政治的阴影开始从普通人的生活中渐渐退却,大多数人似乎都可以以平民的身份平等竞争。平民成为有了主体意识的一个新的庞大群体,第三代诗人们正生活在他们中间,且身具着平民的身份。于是,他们决意表现这种最普遍的人生,他们宣称自己要“像市民一样生活,像上帝一样思考”,在创作中力图使诗歌世俗化、平民化,切近最凡俗的人生。在这样的追求这下,他们的创作呈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
首先,是他们诗歌中对“反英雄”的人生体验的反复表述。
所谓“反英雄”,是指那些生活中最为庸常的生命。许多第三代诗人从人的生存本能出发,在诗歌中体味和反映凡俗生命中所有的内容,如爱恨、生死、苦乐甚至一饮一啄、睡觉如厕。
这类作品中的代表是王小龙的《纪念航天飞机挑战者号》,这个曾经被整个世界瞩目的悲壮的场面在这位诗人的笔下,呈现出荒诞的一面:
这一瞬间改变了什么
这模样古怪的混血儿突然失踪
借助烟雾浓浓的掩护……
没消化的早餐三明治
天空中闪闪亮亮
这种描述也许是真实的,但它却将世界新闻界视为英雄的那位 志愿升空的女教师的形象完全荒诞化了,从而解构了一个英雄的存在。
如果说王小龙的作品带有对英雄刻意的反悖的话,那么于坚的《尚义街六号》则是完全陷入到对凡俗人生的描划中。这首很长的诗以琐琐碎碎的方式托出了一群经常在“尚义街六号”相聚的年轻人的生活片断:
法国式的黄房子
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
喊一声 胯下就钻出戴眼镜的脑袋
隔壁的大厕所
天天清早排着长队
……
诗中写到这些朋友们常常在老吴家中聚会过夜,而在诗的结尾,大家各奔东西:
大家终于走散
剩下一片空地板
像一张旧唱片 再也不响……
长诗采用了完全口语化的表达方式,琐屑零碎,但细细读来,却有一种抒缓几至哀伤的味道。而这个结尾,则给人一种人生平淡而又无常的凄凉感。
其次,是第三代诗人作品中刻意追求的反崇高的冷抒情。
第三代诗人惯于以凡夫俗子平淡的平民意识代替朦胧诗人们理想主义的英雄气概,显出一种近乎玩世不恭的黑色幽默。如《有关大雁塔》中对人们登塔观光情景的漠然处理。
第三,是他们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反文化的现代口语和语感的应用。
口语词汇与语感的应用,从我刚刚引用的《尚义街六号》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至于“反文化”这一主题的表现极至,则可以用张锋的小诗《本草纲目》来作为代表:
一两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
三钱李商隐的苦蝉
半勺李煜的一江春水煎煮
所有的春天喝下
都染上中国忧郁症
短诗对中国古典文化中许多著名的意象进行了调侃式的借用,解构了其中悠然的韵味,并对中国文化的阴柔、缺少阳刚之气表示出不满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