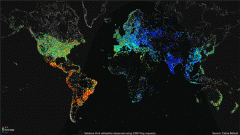以有关天台山道教的唐诗为对象
道教文化与诗歌意象——以有关天台山道教的唐诗为对象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陈再阳 时间:2015-12-10 17:46:53 次 繁體中文版 手机访问道教之音
通过描绘自然界的景物,创设诗歌的艺术境界,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大多数诗歌都是这样。诗人在创作时,面对丰富多彩的景观物象,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地取舍。客观地说,这些物象的本身是纯自然的,但在进入艺术作品之后,它就带上诗人的主观色彩。尤其,当某种物象长期地、经常地被作为某一特定的文化符号而使用时,它的自然属性显得更加微弱。我们发现,在唐代有关天台山道教的诗歌作品中,诗人们或为了营造特定的宗教氛围,或为了表达某种宗教情感,经常使用某些物象,这些物象,有的在使用中完全脱离了它的自然属性,变成了一个道教文化符号;有的虽然保留了它的部分自然属性,但明显呈宗教化趋势。兹就最常见的几类诗歌意象进行探讨。
一、“朱阕青霞断,瑶堂紫月闲”
月是中国诗歌中的传统意象。静夜望月,往往产生对故乡、故友和离散亲人的思念,如《古诗十九首》里那位思妇,当“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时,强烈地思念征夫而夜不成寐;曹丕《杂诗》中的那位游子,“仰看明月光”而“绵绵思故乡”;杜甫被囚长安时,看到天上的明月,想起自己的妻儿(《月夜》),他们因睹月而思亲,又借月寄托思念,“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子夜四时歌秋歌》),在他们笔下,月亮成为世俗感情的载体。而在有关天台山的道教诗中,月亮却很少作为人间亲情的寄托,大多服务于宗教。且看:
朱阕青霞断,瑶堂紫月闲。(张说《寄天台司马道士》)
诗人以丰富的色彩来建构仙境之华丽堂皇。称月为“紫月”,则此月已被道教占有。因为,这里紫色的运用,一是与道教的紫辰崇拜有关,中国古代星象说,将天上星座与人间帝王卿相相配合,认为紫微垣(又称紫微宫)乃紫微大帝所居,紫微大帝是元始天尊的化身,仅仅受玉皇大帝支配,统帅三界星辰和山川诸神,为一切现象的宗主,能呼风唤雨,役使雷电鬼神。[1](P911)由此留下了星辰信仰的痕迹。二是紫色是道教修炼境界中的特殊颜色,内丹外丹的种种修炼行为,都常以之为名表示珍异。比如用于外丹修炼的就有“紫粉”、“紫铅”、“紫琼”、“紫方天”、“紫珠芝”、“紫仙芝”、“紫金还丹”等,用于内丹修炼的有“紫霞”、“紫金丹”、“紫金莲”、“紫金明”等,故为道人所认同、喜爱。诗人将一切景观安置在紫月的笼罩下,营造了富丽堂皇而又静谧幽寂的仙境氛围。再看:
秋风吹月琼台晓,试问人间过几年。(孟浩然《玉霄峰》)

仙境一日,人间百年,秋风瑟瑟中照洒在琼台上的这轮月亮,还属于凡间吗?“门标赤城霞,楼栖沧岛月”(李白《天台晓望》),楼观上悬挂的这轮月也不是人间的月,它属于海上仙岛。而“坛场月路几千年,往往笙歌下天半”(灵一《妙乐观》),则以象征时间永恒的明月点出了千年古观的历史,由此引出对仙人活动的遐想。至于“往往鸡鸣岩下月,时时犬吠洞中春”(曹唐《刘晨阮肇游天台》),“惆怅溪头从此别,碧烟明月锁苍苔”(曹唐《仙子送刘阮出洞》)中的月,则本来就是仙界的月了。
在人们普遍的观念认知下,日光芒四射,气氛热烈,身处其中,容易兴奋,导致欲念滋生,此乃修道之大忌,而得道成仙的前提是“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与道冥一,万虑皆谴”。相对日而言,月是阴性客体,它本身之静谧幽冷的形象,加上易使人产生静夜的联想,正符合了道教主静守一的修炼工夫。此外,月光较日光幽暗,色呈银白,半透明状,具有朦胧飘忽的特点,这与仙人境界也相符。因此,除了将月“仙化”以外,诗人们也用它来制造仙家阆苑的氛围。有的“制造”寒凉:
石标琪树凌天碧,水挂银河映月寒。(李绅《望华顶峰》)
半夜人无语,中宵月送凉。(任翻《宿桐柏观》)
月寒岩嶂晓,风远蕙兰芬。(郑薰《冬暮挈家宿桐柏观》)
云开孤月上,瀑喷一山寒。(刘昭《禹福圣观》) 有的“制造”静谧:
淡然意无限,身与波上月。(常建《白龙窟泛舟寄天台学道者》)
五峰转月色,百里行松声。(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
影殿山寂寂,寥天月昭昭。(皎然《宿桐柏观》)
常时爱缩山川去,有夜自携星月来。(方干《赠天台叶尊师》)
因思石桥月,曾与道人期。(贯休《春日行天台山》)
青蛇绕地月徘徊,夜静云闲鹤未回。(吕洞宾《游福圣观》) 有的“制造”朦胧:
坛上独窥华顶月,雾中潜到羽人天。(李绅《题北峰黄道士草堂》)
洞里有天春寂寞,人间无路月茫茫。(曹唐《仙子洞中有怀刘阮》)
星精观空泣海鬼,月涌薄烟花点水。(贯休《寒月送玄道士入天台》)
此外,也有“制造”高峻的如“人在下方冲月上,鹤从高处破烟飞”(周朴《桐柏观》),还有“制造”清美的如“落花流涧水,明月照松林”(杜光庭《山居》),这些趣味各异的月,从不同的侧面大大强化了仙境的宗教氛围。当然,这也只是就其在诗中表现的侧重点而言,事实上,诗人笔下的这些月,往往兼有以上所列各种效能,是多种仙界特征的综合体现。
二、“白云天台山,可思不可见”
白云、烟霞也是纯自然景观,是中国诗歌中的常用意象。但在有关天台山道教的唐诗中,它们也带上了浓重的宗教色彩。

《庄子·天地》有“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有此神话原创,加上白云本来就在天上人间自由飘荡,后来,在道教中,白云同鹤一样,也成了神仙的交通工具,神仙们腾云驾雾,自由往返。于是,当“准神仙”的道士出行时,诗人们自然联想起白云这一神仙坐骑:“羽客笙歌此地违,离筵数处白云飞”(宋之问《送司马道士游天台》),司马承祯的别宴还未享用完,他的坐骑就已等在那里了;“人间白云返,天上赤龙迎”(《寄天台司马先生》),赤龙接上天,白云送下地,成仙了的司马承祯让崔湜羡慕不已;“一朝琴里悲黄鹤,何日山头望白云?”(《送司马先生》)痛别之际,李峤向司马承祯真诚地问:当我伫立山头望眼欲穿,到哪天才能见到您乘白云回来?甚至,当司马承祯永别人寰时,也是白云接走了他:“(司马承祯)卒于王屋山,时年八十九。其弟子表称:‘死之日,有双鹤绕坛,及白云从坛中涌出,上连于天,而师容色如生。’”①与白云充当仙人坐骑这一文化含义相应,或许还因飘忽不定来去无踪的自然形态,迎合了神仙的变幻莫测逍遥自在,如孟浩然之谓“鸡鸣见日出,每与仙人会。来去赤城中,逍遥白云外”(《越中逢天台太一子》)。白云,也成为仙风道气的象征,“王乔已去空山观,白云只今凝不散”(灵一《题王乔观傅道士所居(妙乐观)》),“白云天台山,可思不可见”(沈如筠《寄天台司马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