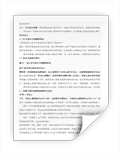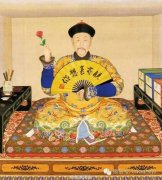故宫里的手艺人:在给故宫文物治病的高手(2)
故宫的老师傅们大多是十几岁就进入故宫做学徒。史连仓3岁的时候就住在故宫边上了。他的父亲1982年从故宫木器组退休后,他接班进入了木器组,从小到大,50多年的时间就在故宫度过了。故宫对史连仓和这些拥有匠人之心的师傅们来说,不仅是一份工作。
镶嵌组的孔艳菊,大家都喊她孔孔或孔姐,她手下的文物,从原料到一件艺术品,经过怎样的雕琢,有哪些经历,都是她跟文物很有意思的对话。不仅如 此,修复还会加入现在修复者的手艺、对美的理解等各方面的因素进去,“你是凑合凑合还是不能凑合、认真对待。这里面有一种精神在,所以你觉得它是活的。” 孔艳菊说。
现在的师傅们,可以看出上一个修复者当时的技艺如何,甚至可以猜测他当时的心理和外貌,这是一种穿越古今的奇特体验。
书画作品,往往百八十年修复一回。片中,书画组正在修复一幅贴在门扇上的清朝大臣的画,书画组的书画修复科科长杨泽华推测道:“这浆糊抹的不太厚,不知道那人(上一个修复者)长得什么样,一定是高高大大的。”修复室里一阵欢笑。
不一样的故宫
“解说n、l不分。”观众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评论里批评解说的口音。叶君笑着说,这是故意为之,本来就不打算找一个专业的配音。
该片解说配音曹志雄是湖南人,曾经是《鲁豫有约》的制片人,现在的职务是《超级演说家》的制片人。叶君认为,“这虽然讲述的是故宫,但是他们并不想做成一个就传统说传统的纪录片。我们背着唐诗宋词长大,但是我们也是用手机、电脑的现代人,经过现代趣味的处理,现在的年轻人更容易接受”。
而这部纪录片能够让年轻人喜欢,更重要的是《我在故宫修文物》里的故宫并不是深宫墙里沉闷、严肃的故宫,故宫里的老师傅风趣、幽默、生活化,同时片中还有一帮爱说爱笑的年轻人。
拍摄期间,故宫里的杏子成熟了,落在地上的杏子成了蚂蚁的美餐。工作放松的间隙,木器组的成员们拿出棍子,开始了收获。在故宫里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这里绿意盎然,他们可以在瓜果飘香的环境里工作、生活。
有些树是他们自己种的,有些树是他们的师傅种的,还有些树,是生活在明朝或者清朝的人种的。
种些植物、养个鸟、逗逗猫,外加上朝八晚五、不能随意加班的工作制度,这些都让人羡慕不已。但是对于文物修复,这些“绿灯”都是为了让师傅们更加集中地工作,一点松懈,在文物修复上,都可能是无法挽回的伤害。
王津修复的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它原来的主人是乾隆皇帝,一个小毛病也许就得调上个一天半天,这个过程还得反反复复。王有亮在堆满调色板的工具桌上调配青铜器的颜色,不顺利时一个颜色都要调上一个星期。
这是个急不来的行当,与当下快速的生活观念格格不入。王津说,他的时间感与宫外的人们是不同的,“干这行最重要的就是坐得住”。
镜头下,纺织品修复组的陈扬正在办公室的一角织缂丝。在古代,缂丝的使用者非富即贵,皇帝龙袍用的就是缂丝工艺。一个熟练工一天也只能织出几寸缂丝,因此现在人们已经不用缂丝了。陈扬说,即使是苏州的年轻人都忍受不了缂丝。
2009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了纺织品修复组,这里没有所谓的师傅徒弟,参与工作的都是年轻的女孩。在进行特殊修复的时候,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不能开空调,“还不能抹粉底,不能化妆,不能喷香水,不可以做指甲”,女孩子们迅速地补充着。
最近几年,故宫每年大约吸收四五十名应届毕业生。在文保科技部,如今年轻人占了一大半。5年后,随着老员工慢慢退休,故宫将有三分之一的员工替换成新鲜血液。
虽然许多观众看过纪录片,纷纷表示要到故宫修文物,但是其实很多年轻人并不愿意到故宫工作。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孔艳菊在进入故宫博物院之前,和大多数人一样,以为这里只是一个旅游景点。孔艳菊笃定地说,刚从学校毕业来这里工作时,每个人都很难适应,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才能适应,“一进入大宫墙,外面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就如同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孔艳菊说,刚入职时,故宫里安静的让她都不敢说话。
如今她已经是故宫里的老员工,也是镶嵌组的科长,她组里的年轻人也渐渐多了。但是在文保行业,即使已经工作5年的修复师罗涵,在这里还是个新人。
故宫在接受这些年轻人的同时,也引进了许多现代技术——谷歌眼镜、3D打印技术、扫描等,都慢慢成为故宫的装备。与此同时,面粉熬制的浆糊、猪血、生漆、鱼鳔等原始的技术也仍旧在这里流传。
如果没有《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我们与展厅里品相完整的文物擦肩而过时,很难知道它们曾历经断裂残损和惊心动魄的修复。
文物是过去式,但修复文物是正在进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