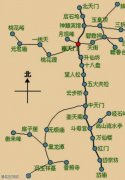【过年那些事】和父母在一起的春节印记
今天是正月初三,雨过天晴,春意渐暖的天气一下清新了许多。这几天,老是想着过去父母在时的春节,也许今年的春节过得有些平淡,除了年前家人团聚,年三十看春节晚会、看亲友发来的祝福短信、接听亲友的拜年电话、出去拜年外,似乎一切都和平时生活没有多大的不同,这个春节确实感到平淡了许多。
时过迁境,物也非,人也非。回想起有父母的春节,真的是梦回萦绕,感慨良多。那时的春节,正如着名作家冯骥才说的那样,“中国人追求什么,中国人的生活需要什么,在春节里表现得最深刻;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人的现实精神,在春节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人的现实和理想是混在一起的,中国人过年的时候,必须比平时吃得好,穿得新。中国人是要在春节的时候把理想现实化,也把现实理想化,所以春节是放大了的生活现实,对中国人说,”年“有特殊的魅力,这是中国人的伟大创造”。在我的印记里,我和父母过的春节就是这样的春节。
印象深刻的还是改革开放前的春节。那时,虽然物质匮乏,但比起现在的年味要足得许多。在我的过年感觉中,过年要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年三十以前的“忙年”,接着就是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的“过年”,从“忙年”到“过年”才是一个完整的“年”,大家为了迎接新年,都把未来一年的期待都寄托在“年”上,所以大家再辛苦、再劳累,都乐于“忙年”和“过年”,在“忙年”中迎接新年的到来;在“过年”中享受新年的喜庆和欢乐,祈福来年的幸福。
在我看来,那时的“忙年”是从领取购买年货的票据开始的,春节临近前一个月,所辖粮店就要到居民点来发放购买年货的票据。那时都是计划经济,国家把城市居民生活用品都计划到了每个家庭、每个人,购买的年货也一样,每家凭“购粮证”领取各种票据,如吃的有粮票,黄豆票,杂糖票,沙糖票,食用油票、豆腐票,肉票、鱼票、禽蛋票等等,穿的有布票、棉花票等,还有烧火的煤炭票、柴火票,那时没有这些票据,即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
有了这些票据,就要开始“忙”着买年货回来。那时买年货必须起早床,远不如今天的市场如此丰富而多样化,今天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立即买到。那时,我得和母亲凌晨2-3点钟起床,冒着寒冬腊月的雨雪赶去菜市场排队买年货,在凛冽的风雪中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为了多买几样,一个早上要排上好几个长队,有时为了多排队,人们就把自己买菜的篮子、簸箕、砖头等充作排队的“我”放在队伍里跟队。由于物资短缺,有时快要排到前头了,营业员突然说没货了,只好遗憾地第二天凌晨再去赶早排队,这样的情形时有发生。那时买年货,菜场要排队,粮店要排队,副食品商店都要排队。
其实,我家那时年货来源,除了在武汉市场上买的,还有来自乡下的年货,也就是小哥从农村买回来的年货。那时,小哥医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远离武汉的农村当医生,作为医生的他自然受人尊重,所以,他在农村也能买到一些年货,尤其是那些很新鲜的鱼肉,每年年关前,都是我踩着自行车,或三轮车到武汉关码头去接小哥回来,拉回他带回的年货,小哥在农村当了十年医生,年年如此,所以,我家的年货比起别人家又显得丰盛许多。
买回来了年货,还要“忙”着去做“年饭”,磨汤圆、炸肉园子、炸翻散、包饺子、煨排骨汤等等,都是武汉人不可或缺的“年饭”。做这些美味佳肴的“年饭”都是以母亲为主,我和小哥当配角。虽然和母亲一起忙得很辛苦,不分昼夜,但也确实能在“忙”中慢慢感到年味的浓郁和快乐,可谓累并快乐着。其中,印象深的是磨汤圆,那时吃上汤圆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时市面上根本就没有如同现在市场上包装好的半成品汤圆买,汤圆都是自家磨出来的,首先,要把糯米泡好,再去借来磨汤圆的大石磨,每年都是我和小哥轮流转动着那笨重的大石磨,母亲一勺一勺地将泡好的糯米喂入石磨小孔里,随着石磨的转动,糯米浆慢慢地从上下石磨中间流出来,磨完糯米后,再将糯米浆倒入米袋过滤、晾干,最后再才能搓成园溜溜的汤圆。所以,每年过春节磨汤圆是一项很耗时、很劳累的劳动,尤其是快到年关了,母亲都要熬夜磨完汤圆,我那时年纪小,有时熬不过夜就睡着了,可母亲却自个儿要磨到第二天天亮,每年春节,母亲都是这样过的。
除了“忙”着买年货,还要“忙”着年前大扫除、做卫生,母亲是一个很爱整洁卫生的人。临近年关,有2件事她是必须要做的,一个是粉刷墙壁,一个是床上用品和家人新年要穿的衣服必须浆洗干净、整洁。其中粉刷墙壁都是我和母亲一起刷。那时每家都是烧煤炉,三家共一个厨房,每家都是烧柴生火,煤烟气时常熏黑了整个厨房和住房,所以,每年我都要和母亲去房管所买回粉墙的白石灰泥浆,那时房子不大,不到20平米,我自己粉刷墙顶和墙面要花上一到两天的功夫,粉刷后的房屋自然亮堂了许多;还要将门窗用红油漆再漆刷一遍。然后,再洗涮地面的每一个角落,不落灰尘;屋里家具都要抹得一尘不染,床上被子都要叠得整整齐齐,平平整整。这一切都是为了家里亮亮堂堂、整整洁洁的过大年。
就是在这样的“忙”年当中,我从小耳濡目染地感受到了家人的团结与默契,感受到了辛苦的劳动带来的愉悦和收获,感受到了自己融入其中的责任和父母的温情,感受到了春节临近的喜气和期待,也感受到了对新年的憧憬。
到了年三十,就是“过年”的开始,父亲写对联,大哥画年画,吃团年饭,以迎新年,相聚酣饮,其乐融融。
吃团年饭是“过年”重头戏,母亲最重视,每天她起得最早,大清早就开始准备大年初一团年饭,母亲很能干,每年过春节,桌子上都至少要摆上10个菜,都是她亲手做,我最喜欢吃母亲做的湖南的“酿豆腐”和“酿辣椒”,其中的美味至今难忘。
父母有很多亲朋好友,他们很舍得待客,和周围邻居关系都很好,所以,我家吃年饭时,除了家里人,还时常有周围相好的邻居和武汉的湖南老乡座客,大家济济一堂,过年的气氛很热闹。对于那些关系特别好的邻居和湖南老乡,母亲每次都要派我出去当使者,去邀请亲戚和友人到家里团聚过年。有时还有远道而来的友人和家乡的亲人,即使家里住不下,也要搭上临时床铺待客,真可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