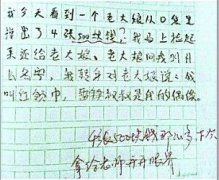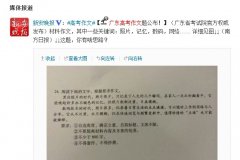《散文选刊》2015年12期抢先看
正文 字体大小: 中
《散文选刊》2015年12期 抢先看 (2015-11-25 11:33:04)
实力散文家之席慕蓉——乡关何处
那天早上,由于我刚好坐在车门口第一排的位置,所以,当中途停车,把等候在路边的一位女子接上巴士来的时候,我自然向窗边挪过去,她就坐到我的旁边来。
先是匆匆颔首向我打个招呼,然后就直视前方,不再言语了。
我却不太习惯。好歹都是同车旅游。礼貌上试着交谈一下,应该比较自然些吧。
想不到,我刚侧过身去,还没来得及开口,她就转过头来对我说:
“我不是你们一团的,只是刚好有位波兰诗人邀我来参加今天的活动而已。”
面部没什么表情,讲话的速度很快,说完就又把头转回去,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我几乎是被噎住了。只好也转过头来面对右边的车窗,笑脸一时还收不回去,心中却有了怒意,莫明其妙,谁怕谁啊?你这西方人不想寒暄,我这东方人也不见得非要理你不可。
是的,我们之间最初的分野,就在于此。从外表来分,只是西方与东方的差异而已。
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我应邀参加以色列的国际诗歌节,这天是会后旅游,一车子的诗人从特拉维夫出发,直奔死海而去。
越走景色越显荒凉,都是寸草不生的山丘,后座有些人在高声谈笑,我与她依旧互不干扰,保持沉默。
走着走着,窗外是不断下降的路面,路旁灰白的岩石层层堆叠,队伍里有位导游,忽然出声提醒我们,说前面就快要经过那处发现了“死海经卷”的洞穴了。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屏息等待,再顺着他的手势往车子右边的山上望去,果真遥遥看到,在山坡高处的岩石之下,似乎是有处略显低矮的洞口。
珍贵的经卷就藏身于如此荒凉的山野之间吗?
我听到邻座的女子就在我身侧轻声吁叹,想她也正和我一样,还伸长着脖子往那已经逐渐远去的山坡上方眺望着吧。
其实,这时候的我已经不生她的气了。近几年,在旅途中遇到不少类型的怪人,有的人真的是不喜欢说话,像她这样开门见山地先宣示了,也没什么不好。
我静静地继续观看窗外景色。不过,这些色彩灰白干涩的石头山丘,实在不能称之为“风景”。不禁在心中自问,这就是离散了千年又千年的犹太人念念不忘的故土吗?
“我母亲生前最后一次的旅行就是到以色列来的。”
有声音从我左侧传来,用的是英语,是在对着我说话吗?
转过头来,果然,是我的邻座,她浅褐色的双眸正对着我。
还继续说下去:
“我母亲在那次旅行所拍的最后一张相片,就是在死海附近拍的。”
我心已经变得非常柔软,开始仔细地端详起她来,是个三十多岁、装扮朴素的女子,微胖的脸颊,一头蓬松的棕色短发,她还在继续对我说话:
“那张相片上的她是微笑着的,很愉快的样子。所以,母亲过世之后,我一直也想来看一看以色列,重走一次我母亲走过的路。”
见我对她微笑,她略显羞涩。但是,我相信自己凝视着她的目光一定鼓励了她,所以,就再继续说下去: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我们家虽然是波兰的犹太人,但是,我生在瑞士,长在瑞士,对父母谈话中的波兰虽然也不是不感兴趣,却从来没有想回波兰去看一看的念头。我念的是化工,现在也在学校教书,我在瑞士过得很好。我觉得父母的前半生好像只是一页应该早已经翻过去的历史一样……”
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好像要想一想再如何解释。然后,低垂了双目,她说:
“在我父亲逝世之后,日子好像还可以像从前一样过下去。但是,等到母亲也过世之后,我就没办法了。有个什么东西一直在我心里捣乱,逼得我非采取行动不可。所以,我终于去了一次波兰,去好好看了一次我父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不一定是他们的家乡,而是那整个地方的感觉。好像非要这样走一趟,才能重新回到瑞士,重新生活下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明白这种感觉吗?”
语气如此急切,想是心中贮存已久的思绪都在此刻争先恐后地要找人倾诉吧?所以不得不抓住眼前这个东方女子作为对象,可是,又怕她不能了解自己的苦楚。毕竟,东方与西方,相隔那样遥远,除了地理上的、文化上的,应该还有心理上很难跨越的距离吧?
在当时,我们两个人谁也没体会到,关于“远离乡关”以及“追寻母土”这两个主题,是生命里最基本的主题,并无东方与西方之分。所以,我只是很自然地回答她:
“我想,我应该是可以明白的。”
然后,我就用很简短的几句话,向她说明了自己的身世:与她相同之处,是我也是个生长在他方,远离了族群的蒙古人,并且一直到中年之后,才见到了父母的故乡。
而与她不同之处,则是母亲虽然早已过世,但在我还乡之时,父亲却仍然健在,并且很高兴有一个孩子终于可以与他分享关于蒙古高原的一切。今与昔,明与暗,所有的沧桑变幻,在整整九年的时光里,我们父女之间几乎是无话不谈,可是……
可是,我告诉她:
“去年冬天,父亲走了之后,我才忽然发现,有许多非常重要,甚至非常基本的问题,我都忘了问他。我怎么这么大意呢?如今的我,心中充满了懊恼与悔恨,父亲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我竟然没有问过他一次,这么多年的远离乡关,他是靠着什么样的力量和勇气才能熬过来的?”
就在这个时候,心中累积的疼痛使我不得不流下泪来,坐在我身侧的她,用着更急切的语气向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