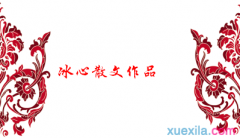《散文选刊》2016年11期抢先看
卷 首
伟大的散文在一切写作之上
⊙于 坚
⊙杨 婕
八月三十日,二○一二年。搬家当天早晨,叔叔来清点家具结算水电费,进屋探看四周,夸我维持得好:“女儿的房间果然干净!”叔叔在桌前记账,零散道些以后回来请我吃自助餐的话,发出一贯的嘿嘿笑声。我不敢看叔叔,背过身弄东弄西。搬家公司的先生将对象一箱箱往外搬,房间掏空,叔叔事毕,喊我名字说声:“杨贼再见啦!”
我挥挥手,忍不住哭出来,叔叔溜身利落地走了。
那批最初带进房间的行李,以及几年来添加的种种,都叠层打包塞到车里。我和那些东西一并坐上车,下斜坡,分分秒秒远离了房间,远离店面。车辆加速,风景一窗窗快转,还是不能无缝迁徙。
前座搬家公司的先生笑了,他从没遇过客人搬家哭的:“感情太丰富!这有什么好哭?人生不就是搬来搬去,你以后就习惯了!”
前几天买的花生塞在包包里。我一边注意花生不要压碎,一边手撑拉环,颠颠簸簸下山。转往台铁,五十分钟出站,走过站前圆环,等熟悉的号码驶来,开往位在郊区台地的校园。
踏进消夜街,街底斜坡向右,绕过已不属于我的房间。巷弄尽头,两点钟方向便是自助餐厅了。
离晚餐尚有一段工夫,铁卷门半拉下,我远远走近,来路程程退开。拨打叔叔手机,接通道马上下楼,几分钟后铁卷门升高,叔叔阿姨弯身出来,叔叔略发福些,阿姨头发烫卷了。他们未料我要来,我拿出花生,有些紧张,阿姨先发话:“哎唷你怎么知道叔叔最喜欢吃花生!你跟叔叔慢慢聊,阿姨去煮饭!”
我实则误打误撞,像签约那天第一次踏进自助餐厅。
那是三年前的下午。初冬微寒,老旧店面显得温暖,我和母亲看过房间,随阿姨来到店里。店内光线昏暗,玻璃印满刮痕,雾气般掩住街景,非用餐时段,不见客人。
阿姨端出一盘薯条,母亲正要推辞,阿姨说不是特地炸的,早上小儿子顾店,当作给他的奖励,刚好多炸一点,还想夹什么菜自己拿,吃饱再走啊。我们礼貌性地拿了几根薯条,离去时还剩少许。食物的气味混合着周边氛围,自助餐未有多余陈设,毫无宣扬。
“我们会把她当自己女儿照顾,你们放心啦!”阿姨告诉母亲。
从房间到自助餐厅步行仅需三分钟。刚搬进房间,我每每造访自助餐厅,皆为房间细琐,进去店面总见烟气蒸散,叔叔阿姨挥锅铲端菜盘里外出入。炒菜喧嚣,到厨房门口他们才发现我来了,通常阿姨掌厨,问候一声继续蒸煮,叔叔负责招呼,管房子的事归他。
那段时光我中午一向早吃饭。有几天上午的课十点结束,一段空档正好处理杂务、买午餐。我常趁那时去店里,每回叔叔皆问我买便当,我的脾胃挑食而专情,相同菜式能吃上个把月,已有固定店家。起初婉拒几次,但早开的店不多,饿就加减买,时日久了挑到合口味的菜,便养成吃自助餐的习惯。叔叔得空就和我聊几句,在那些装饭拣菜的步骤里日益熟起来。
来得太早,惯吃的菜还没摆出来,叔叔阿姨一边炒菜一边包工厂订的便当,抽手替我盛饭端菜。去的次数多了就更家常,让我进厨房,蹲在推车旁翻拣,钱搁柜台,自行打包。便当都算我便宜些,倘若叔叔拜托我张贴房子出租的布告,那次就不收钱了。
我的便当固定熏肉配高丽菜,不时也换梅干。阿姨是客家人,梅干扣肉煮得极香,我不晓得地道不地道,一吃就爱上。梅干扣肉大约两周卖一次,不定哪天会有,得知我爱吃,每逢去店里,假如隔天要卖,叔叔便会提醒我一声,有一次没过去,叔叔特地打电话来。
偶尔过节,他们便替我加菜,夏天的粽子,秋天的柚子。夹完便当后,阿姨会小声叫我留步,等别的客人走了,再塞给我带回房间,节庆就爽口 些。
我几乎天天行经自助餐厅转回房间,过了店招,便到达房间所在的巷弄。我时常停下脚步,为房间细务踏进店里,没上门,也碰到叔叔出来送便当,熙来攘往的街道上,他会用台湾腔普通话越过重重人群不太标准地喊我:“杨贼!杨贼!”每当我低着头非常疲倦地走在路上,思绪晃到哪里浮浮荡荡,一辆机车过去,我便被叔叔的招呼唤醒,思绪不动声色落了地。
我在那间房间学会照顾自己。基本的衣食住行,面对自我,孤独。无论何种技能,皆比同龄之人晚熟,凸槌时,少不得叔叔阿姨前来救火。
一回洗衣机故障,脱水功能失效,打开盖子,每件衣服都浸着水,重洗再丢烘衣机,连烘两次仍湿淋淋,只好整篮衣服滴水搬回房间。阿姨来,说之前有房客用钓鱼法洗衣,现在衣量超载就会坏。阿姨踏进房间,见晒衣杆满满两排,教我一次该放多少衣服,踩过走廊、电梯摊摊水洼,一句责备也无,只问花了几块钱洗衣,塞钞票到我手里。
保险丝烧坏,房间跳电,叔叔提来照明灯,告诉我店面二楼有空房,晚上不方便就去睡。我钥匙用了一年都乱转,有一天缺乏手感便堵在门外,以为门锁生锈,倒油也开不了,正是晚餐时分,叔叔放下事务,风风火火过来,一扭就开。叔叔嘿嘿笑几声,教我用钥匙,回店里继续忙碌,叔叔道:“你念文学的,生活的事比较不懂啦!”
自助餐厅休息时段,叔叔常来巡视、打扫。见房间灯亮着,便会敲门,拿挂号信,交代房间的事,有时不过打招呼,也没说什么。叔叔走前,总笑着告诉我:“那叔叔先回去忙了嘿嘿!有事情再打给叔叔!”
镜头倒转。大二那年初夏,夜半我在房间痛哭,敲门声蓦地响起,只得硬着头皮开门。叔叔站在门口,看了我一眼,轻声叮咛:“爸爸妈妈不在这里,你就把叔叔阿姨当成自己的爸爸妈妈,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讲,我们能帮的就帮,不要自己闷着,这样不好。”
过几天去买自助餐,闲聊几句,叔叔问心情好多了吗?“叔叔知道你是个用情比较深,比较细腻的女孩子。”我暗暗吃惊。我向来只跟叔叔阿姨说些生活琐事,天气、食物、居住、考试,关于情感,关于内心,只字不提。
那些日常片刻,叔叔用他的方式理解了我,即便他所知不多,我所谈亦不多。而那样的理解,在长年独居、不喜同群体往来的大学岁月里,已是我与周遭人事最密切的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