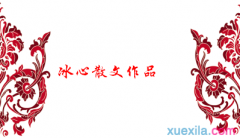《散文选刊》2016年11期抢先看(2)
我对人际纷扰戒惧,曾有过的幻想与渴望,早随之灰飞烟灭。但和叔叔阿姨相处,一切仅是简单的细节,往来之间,终能踏实地触及自我。叔叔阿姨是很寻常的夫妻,哪条巷弄皆会出现的一对夫妻,因为寻常让人亲近。
那几年难以言说的青春起伏里,他们的素朴,成了提点我的一种要领。
也就是那段日子,我为房间写了一篇散文,细述里外物事,得了文学奖。叔叔在结尾轧上一角,我想叔叔阿姨不看这些,便不太提起。
搬家前几天,我把两年前的作品附在卡片上,拿到店里交给叔叔阿姨。阿姨曾笑笑地腼腆告诉我,她年轻时也喜欢读诗,席慕蓉噢。这些年的蒸煮炒炸中,那款脆薄的兴趣应该也沦为一种过时的菜肴。说不定那篇散文将被弃之屋角,但这是我跟他们告别的仪式,不得不了。
回想那间房间,虽则装潢好、屋况新,但位处马路旁边,我神经质地怕吵,每隔几分钟车开过去都不得安宁,近处又陆续盖起几栋新房子出租,敲打声终年累月。可我一直住着,不容再住才搬出。
我走得晚,同一批房客六月毕业季就迁离了。那阵子去买自助餐,叔叔常念叨着说:“你也快搬走啦,好像女儿要走一样。”
离开后,我才察觉,那摆满饭菜的店面,比起房间,更先给了我居住的感觉。房间跟自助餐厅始终那般接近,处置房间事项,往往在自助餐厅交办,领房间物什,也和热腾腾的便当一道拎回。在自助餐厅以外的地方遇到,他们常说,从店面忙完过来,等会儿要回店里。找话题问候叔叔阿姨,亦围绕自助餐厅——几点打烊?哪些客人上门?煮什么菜?我几乎错觉自己也在店里有过一间房间。
刚上研究所时过得并不开心,和叔叔阿姨未有联系,仅有一回接到电话,看来电显示是叔叔,以为问我近况,结果只是通知我去拿寄到旧地址的体检表,讲几句就挂了。
后来零碎听见还在那里的友人传来音讯,似乎每逢中文系的人上门,叔叔就容易提起我。叔叔告诉同学:“她就像琼瑶小说的女主角似的!”阿姨有了脸书,想加我却找不到,送出交友邀请,阿姨迟迟未回复,或许仍对计算机太生疏。
叔叔阿姨知悉我申请上交换学生,忘了日程,向同学问起我过得好不好。彼时我尚未前去交换,方短期旅游回来,刚从异地寄出明信片,无须多加解释,他们收到便会明晓。
记忆窝里反,距离山重山。人生总是如此,但我对记忆和距离执着。
学期过完,回到那条街。房间是进不去了,自助餐厅的铁卷门缓缓拉开,就跟签约那年冬天一样暖。陈旧空气里,叔叔说起,上次晕倒送进医院了,现在要多休息,周六不开店了。叫我包个便当吃,傍晚还得赶回学校,叔叔便改口到隔壁买饮料请我喝。
这几天才跟阿姨念到我:“在想打个电话给你,又不知道怎么打就没打嘿嘿!”聊起搬家那天——“叔叔你转身就走了!”叔叔道他不敢看我的表情,才赶快走掉,回到店里就告诉阿姨我哭了。“你是第一批房客,住最久,比较有感情,我们和你缘分深啦!”
叔叔交代,经过附近要回来看看,提早讲一声煮梅干扣肉等你来,再回去就住那栋房子,会替你留房间。“不管什么事,工作啦嫁人啦都要告诉叔叔,你结婚叔叔一定包红包。”
两天后,夜里手机震动,阿姨传来简讯,百来个字,说那天见到我很高兴,祝我早日取得硕士学位,一切顺利。
几年屋事,叔叔阿姨一向电话、当面告知,我第一次收到来自他们的简讯。在这轻薄的年代,仍然有人,打简讯像写一张卡片,有着隆重的心意。叔叔阿姨不雪月风花,也不诗词书画,他们如是不擅表达感情,因此每一句都真实。
叔叔阿姨替我守住了对那里的眷恋,而我曾经以为自己将只是无情之人。
我何其后知后觉。无数次和叔叔阿姨聊及房间细节的时刻,错觉将真正关乎自我的种种,遮蔽或延后了。当时未曾提及的愿望和困扰,在时间磨洗下,终于揭开面貌,还给生活本身,变得不再重要。
如今我在他乡租住,经常不合时宜地想起往事,重读在那间房间写过的字句已觉陌生,那些十九二十岁的心事,从离居到安居的过程。
房间岁月终烟散在平凡的日子里。学生年年轮换,有朝一日房间势必不认得我这第一个住客,但下次回去,我总能在那黯淡里溢着香气的店面中去来,不像外人地,好好夹菜,吃完一顿饭。自助餐厅的陈设,将一直熟悉温暖,一如已经没有契约期限的房间。
彼时屋室都将亮起,让身份藏隐,也让身份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