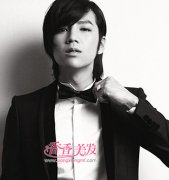我眼中的长江三峡大坝!
2011年6月19日21:30,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蔡其华做客央视新闻频道《面对面》,就开年以来的罕见旱灾——再到6月以后开始的长江中下游流域连降暴雨——这一系列极端天气所导致的旱涝急转是否与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直接相关的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这一期节目的名称为:江河安澜。
当主持人问到:
——外界有这样一个声音说,天气只是一方面原因,更多地还是来自于三峡这样的一个大坝的建成,您听到过这样的声音吗?
蔡其华回答:
——我听到过,我也很愿意跟大家交流。我觉得大家这种疑问还是(出于)对三峡(大坝工程)的关心。我想用这么一个数字跟大家探讨。就是对于这种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主要原因是高空天气的变化所致。什么叫高空天气形势的变化呢?就是从地面到5500米的高程。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三峡大坝的坝顶高程多高呢?185米。185米相对于5500米的高空,无疑这185米是个微量,它还不至于引起高空天气形势的变化。如果说它有点影响的话,它只是在水库的周边,大约十公里的范围内,由于水面的蒸发,使得周边的空气湿度有所增加。从这一点来讲呢,它对缓解旱情,它是正面效应。因此,我们说,干旱是高空天气形势变化所致,三峡(大坝工程)它还没有这个能力、能量来影响到5500米的高程的高空天气形势。。。。。。
就是因为最近再次观看了上述节目的视频,我才萌生了解析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想法。
显然,蔡其华主任的回答,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蔡其华主任“如果说它有点影响的话,它只是在水库的周边,大约十公里的范围内”的说法中,这个“十公里”,无论是在长度和宽度上均为10000米,显然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她说的5500米高空天气形势发生的高度;而她所说的范围,应该不只是一个长和宽的平面,必定有一个高度;为什么呢?蔡其华主任在其后的“由于水面的蒸发,使得。。。”的说法,一方面证明了这个高度的存在,并且10000米要大于5500米;而另一方面则否定了她的立论:因为长江水面即使按照三峡大坝设计的最高海拔蓄水水位175米计算,永远不会高过三峡大坝的185米的坝顶高度。既然水面的蒸发可以影响“周边的空气湿度”,那么,185米相对于5500米是个“微量”的论断就是站不住脚的了。蔡其华主任的论述把三峡大坝工程对于气候的影响巧妙地转移到三峡大坝坝顶的相对高度上来,同时打破了自然环境的整体性架构,可谓是避实就虚!
随着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建成,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烦恼。
长江被截流以后,水流速度变缓——致使江水的自净功能被严重削弱——这是加剧库区支流蓝藻“水华”大面积爆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随着长江大坝的泄洪(船舶通行、腾出库容、发电等),下游江岸、堤坝必然会由于长江水的流速的加快——面临更加猛烈的冲刷,因而,毁堤、决堤的风险就被人为地加大了。
一九九二年后,黄万里教授六次上书中央,陈述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永不可建的道理,均石牛入海!
我曾经在四川叙永县江门镇的永宁河中以及宜宾市沙坪镇的长江上从事采砂石作业。每年的主汛期一过,场地上一片狼藉,不只是顺流而下的鹅卵石和泥沙所带来的淤积,各种垃圾琳琅满目,触目惊心!这还是我所处的永宁河与长江在没有截流的情况之下。不难想象,在长江三峡大坝截流后,就是单单从上游而来的垃圾,就足以拥塞整个大坝库容,更不用说大量的泥沙砾石了。一些所谓的专家公开辩解:——长江与黄河不同,没有那么多的泥沙。我不禁就有了疑惑:随着长江蓄水高程不断地提高,上游被淹没的城市、乡镇、村庄的建筑物垃圾是否会顺流而下呢?长江沿岸被淹没的山体上剥落的植被以及植被覆盖下的已经风化的岩石是否也会顺流而下呢?
三峡工程的运行,打破了湖水原有的吞吐规律。以鄱阳湖为例,每年10月是三峡大坝蓄水期,此时正值江西省的枯水季节,鄱阳湖急需江水补充。但结果是,非但得不到补充,反而被长江低水位拉空,致使出现鄱阳湖湖底现草原的惊世奇观!
就三峡大坝工程而言,当蓄水水位达到海拔175米的设计高程时,才能充分地发挥它最大的发电效能。那么,三峡大坝究竟能够使库区水位在多长时间内维持在海拔175米的高程呢?一旦遇到2011年长江下游的旱涝急转中的旱灾,如果必须为下游补水,那么,发电就将成为泡影。即便为下游泄洪补水,下游的下游,也只能望洋兴叹——真可谓是杯水车薪!如果长江上游出现旱情枯水,我想,只有仰天长啸的份了!
我国著名的水利工程学专家黄万里教授极力反对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建设,奔走呼号!黄万里先生在去世当月曾对探望他的学生留下遗嘱,全文如下:
——万里老朽手所书 敏儿、沈英、夫爱妻姝: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最后还有一行小字)可少死几万人。
黄万里教授在病重昏迷中,还喃喃地呼喊着:“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
在他手书遗嘱的十九天后,怀着无尽的遗憾,黄万里教授离开了我们! 在他的遗嘱中, 除了长江的水利和汉口安危,他没有提及个人及家属一句话;他满腔的深情,火一样的大爱,全部倾注于祖国人民和他为之耗尽了毕生精力、为之忍受了无限屈辱痛苦的江河。他是清华大学教授,早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后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是第一个获得该校工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曾因反对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而被错划成右派。当时,黄万里先生是唯一反对建造三门峡水库的与会者,并与其他专家在会上进行了七天的辩论——舌战群儒!1961年,黄万里教授奉命到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文革”中被贬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