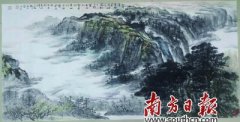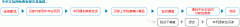[转载]《山东文学》90诗歌专号,感谢评论家!
[转载]《山东文学》90诗歌专号,感谢评论家! (2013-01-22 14:54:30)
标签: 转载
原文地址:《山东文学》90诗歌专号,感谢评论家!作者:木鱼
90后:悄然站起的诗坛新生林
——读《90后诗人专号》散记
马启代
近二十年来,作为诗坛的“旁观者”,对这“体”那“派”、这“选”那“奖”我一直保持着距离。源于个人肯定不无偏颇的诗学认知和写作经验,我的发言越来越谨慎。因为我已无数次地看到许多盛名之下的虚弱和捧杀。我感到,缺乏根性的新诗批评扮演的常常是有些滑稽的角色,好的批评家必须是一个智慧和诗性的读者,甚至是一个优秀的诗人,藉此才谈到专业理论的素养,因为不基于感动的言说无论用怎样的理论术语去修饰都是苍白和空洞的,都类似于蹈空而舞的表演,对我们使用汉语写作的人而言,尤其如此。故而,接读《山东文学﹒90后诗人专号》的稿子,我迟迟不好下笔。在浏览和个别细读之后,我才带着欣喜和惶恐写下自己的几点感受。
首先我对“90后”的称谓保留自己的看法,在没有(现在也不会有)更好更准确的概念界定时,我也不惮于继续使用这一名称。作为近年来(包括台湾诗坛)普遍使用的这种“代际”划分方式,无疑显示了人们更多的期待、更多的焦躁和诗学批评的匮乏。历数新诗近百年来(特别是三十多年来)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实新诗至今处于文体和精神大的积累期,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西方诗学”与“中国诗学”至今未能很好地融合。那些流于表面的“拆解式诗歌批评”和“解构式诗歌批评”不断变幻出或“性别”或“派别”的花样,在不接地气的前提下相互之间争得热火朝天,而新诗写作的实际水准却只能赖于那些边缘和安静的写作者们的寂寞拓进。可惜,与整个时代由“浮躁”到“挣扎”的精神内里相一致,流行的和热闹的诗歌正在失去和麻木着关照大地和心灵的敏感,因而,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同质化、娱乐化和工具化。所以,我不认为“90后”是一个准确而有意义的诗学概念,像“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划分一样,甚至不比“朦胧诗”、“第三代”、“中间代”等的划分更有价值,这种“年龄式诗歌批评”的简单界定很容易掩盖我们对文本本身和诗人灵魂的考辩。在我们大张旗鼓地推进他们一批批群体亮相时,形式往往大于内容,这与艺术本身的代际传承和沉积生发无论就其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是不相符的。因此,我认为“90后”的称谓只是个历史性的锁定,带有符号化的特征。回想一下任何国家和朝代的文学史都是如此,那些带有鲜明美学特色和精神特征的诗歌流派和群体,都是在创作中长期沉淀而具有思想上、精神上和心灵上共同基础的文本集合(其中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也可能在短时间内促成某一流派的形成,那是特例)。当然,我说这些并没有否定现行编辑方略的意思。事实上,自2007年以来,《诗选刊》、《诗歌月刊》等均隆重推出了“90后”诗人特辑,也诞生了许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诗人,许多刊物,像《诗刊》已经在十岁左右的孩子身上不惜篇幅。他们也的确给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和纯真的空气,有的诗人个性鲜明、潜质了得,他们身上的神性和灵性足以令大人们汗颜。中外诗歌史证明,有许多优秀诗人年轻时就表现出卓尔不群的诗歌禀赋,也有许多优秀诗人一生中的重要作品就产生在年轻时期。但毋容置疑,他们中间的变数会很大,许多拔苗助长的举动也许会事与愿违。正是保持着这份清醒的伯乐之心,高艳国先生把稿子发给我时再三说明,这期专号是几位编辑反复筛选的,可能有个人好恶和水平的局限,但一定是遵从编辑职责和艺术良知的“唯质是取”。待我看后,认为大致如此。
第二点我来谈谈自己的阅读体会。唐晓渡先生说自己要重新做一个读者。王家新在上世纪80年代所说的“不断重临的起点”不断地提醒着我,应当说,我是第一次如此放低了自己来集中地阅读“90后”诗人的作品,我试图更多地找到他们写作的内在生成机制和相互沟通的渠道,以免望文生义地做出错判和误导。当然,仅仅靠一次集中的阅读和平时零星的印象是无法给他们做精准描述和宏观定位的,何况他们都在日渐成长和变化,但他们其中的几个人和许多诗中的天籁之音还是不时地擦亮了我、撞痛了我。这些成长于信息化、商业化和网络化时代的年轻诗人,为这个汹涌着各类欲望的时代做了理想的注脚,他们自由的歌唱成为反抗侵蚀、拒绝堕落、护佑人类精神和提升人类心灵的的另一种表达,当然,狂躁和类型化也必然地存在于他们中间,精神的厚度和语言的力度需要生命和时间去锻打。为更切近他们的写作实际,我不想做俯瞰式的素描,而更愿把目光放在一个个可资停留的诗篇上、诗句上和意象上:王冬的诗有着与生俱来的自省和疼痛,他对于生存和时间有着独特的感知,他在短短的几首诗中呈现了充盈自足的诗意世界。他的《接受》所散发出的精神气场必将长久地存在于他的写作中,“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世界”,他说,“我也得接受这样一个世界/我的离开,我的漂泊,我的迷途知返/我的秘密,像一个人的一生/像一个人的来世,像我八岁那年/重新把自己生下,成为自己的父亲”,应当说,这种来源于自身真实历练的醒悟,其所具有的自由精神和批判潜能可能成为推动他进入更高境界的本质动力。因此,他的诗句中含着一种非常纯净的悲悯的力量,如“风也不再发疯,把秋天吹乱一地/油画里的叶子就可以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静止》)、“她开始向下生长,慢慢地回到土里/她不愿意,就使劲得从斜坡上滚下/她抬头的那一刻,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到这世界,越来越像是一块生锈的废铁”(《老祖母》)、“麦田没了,我就/拔掉灰色的森林重新种上/河流没了,我就挖条变质的土块/再引来叶赛宁的月光,蜿蜒流淌”(《我走在北方的土地上》)等等,预示着王冬会有着沉实、宽阔的诗艺未来;相比而言,敖运涛和孤独长沙是两种形式的开阔和坦荡,敖运涛在不失大气的抒写中更多地倾向沉静之美,老练的笔法携带思想的电光把自己的疼痛和泪水化入短促的陈述中,读着他的诗,我甚至怀疑他是一个已经成熟的思想者。面对空旷而多变的大自然,他说:“我要一场大雪,无论春分夏至。我要一场大雪,/像一头白狼”(《大雪》),这已经融入了对生命和历史的感慨,所以他写的好的诗句几乎都是斩钉截铁般的判定句。如“——我掰开来,努力碰击着,/力求擦出星火,看见自己”(《打火石》),再如“——我说那多好啊,要不了多久/她就拥有一个时光之胃,能吃下/更多难以消化的事物”(《一个女孩去贵州支教》)等等,而孤独长沙体现着更为青春的粗粝和狂放,他对诗的文体形式和表达方式均有所注重和探索,仿佛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但马的奔跑显然有着自己的节奏。我喜欢他带着青春血性的直率:“我选择恒河与我一齐降世,十万泥沙俱下,唯我直上”(《我选择》),这是只有充足内在力量的人才敢说出的话,“来吧,一个贴着一个/如对岸青峰般坐着,不要回家”(《最后一夜——寄进退诸兄》)、“二月。我曾抱着一把茶壶呼呼而睡,在长沙的伞中有人送我一阵大雨”(《秋天是突然的》),这是只有高昂精神的人才能发出的声音;相对于其他人,陈有膑和木鱼可能有着对新诗文体和汉语质素的更个性的把握,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注重文字本身的声音,表达上具有节制、内敛的特征,陈有膑的诗富含知性,木鱼的诗蕴藉丰厚,如果他们经过诗艺和生命的磨炼,诗句的铁质和内涵日益饱满,都会有一个很高的升华。另外,陈有膑对汉语有着“预设写作”那种自我演绎的能力,能从一个感触或一个词语出发延展成诗句和意境,如《下雪的日子》,从江非的《雪》触发灵感,层层推演出丰富的意蕴,同时,他的诗句果敢、简洁而质感,如“埋下尸首。像海水埋下一座岛屿”(《悼友人》)、“太阳一出来,我们就老了”(《雪之书》)等等,木鱼所呈现的诗美更为真切细腻,他是那种善于从感觉中提纯诗意和语言的写作者,相对于他人,他的长处在于不肯放过生活中的细节,能把自身的感觉与自然物象相结合,应当说,他更有中国诗学的特质,一些好的诗句皆与古典诗学的血脉相通。如“月亮没有在诗里/火车依旧在月光下奔跑/……/一个节拍一个节拍,钉在我的心上”(《中秋节在火车上所感》),再如“我以火的姿态坐在树上/守住我的思念的桔梗/……/我是孤悬深秋枝头的一只绵羊/天空领不走我,大地领不走我/夕阳领不走我,月光领不走我∥——你不来/我依旧是那只孤悬的绵羊”,其现代性和古典性结合的都比较到位,朴素的诗句中充盈着对万物的关爱,木鱼已经可以确定自己大致的方向;除以上我点到的五位外,高源的舒缓和灵动,如“孩子们闭着眼,睁开小耳朵,童话进进出出/灯光像牛奶一样,浓浓的香。灰尘玩了一天,有点累了/就落下来。时针也是。孩子们也是”(《孩子们安然入睡》),潘云贵的尖厉和冷视,如“红壤、母亲和深埋底层的铁/在我缺碱的指甲里/轻轻地喊着,疼”(《离乡之日》),无歌的舒展和通透,如“我已经没有什么要说了,/包括遗言和情书,/一切早在月光中抵达,/不如让沉默一并下酒,把这世界喝得一干二净”(《致太白》)等都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此外,像余幼幼的《流程副作用》、《偏执狂》,何伟的《三月》,容铮的《衰弱、疾病、爱情》,程川的《十日谈》,周园园的《孤儿》,苏笑嫣的《还是一个姿势的开放》,简杺的《下雨了》,朱光明的《大草原上》,李唐的《纸牌人生》,原筱菲的《摘下霜露》,徐晓的《局外人》,徐海明的《唐山的雪》,乡窅的《河流》,柴彦超的《杞人忧天》,山子的《游吟诗人》,以及青娈的《独坐﹒怀古》等等等等,我所列出的诗句和诗篇可能不是最好的,但肯定是我能记住的其中的一部分。由于篇幅所限,恕我不能列举出更多的名字。无须讳言,即便列出的这些诗人和诗篇,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艺术是永远的未成品。我只是想说明,“90后”的诗人作品是无法用既定的规则去衡量的,除了以上涉及到的优点,除了已经指出的狂躁和类型化,“有句无篇”的现象比较普遍,缺乏构思是当前新诗写作普遍性的痼疾,年轻的诗人需用学养、天分和经验不断地去克服。“诗思”是个诗艺的大课题,郑敏先生在谈到桑恒昌先生的作品时最看重的就是桑先生的“诗思”。“诗思”不局限于“诗的构思”,在这里不谈所谓的理论问题,因为你们的写作就是对理论最好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