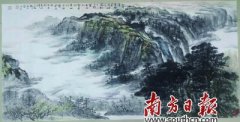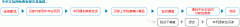[转载]《山东文学》90诗歌专号,感谢评论家!(2)
最后一点,我想简单地谈一下对目前新诗创作的几个想法。这些想法主要是阅读本专号时冒出来的,说出来也许无益,但肯定无害。徐敬亚先生说:“从最高的意义上说,诗歌批评,或者说读诗,永远是一种‘迷失’”,如果这些话属于“迷失中的胡言乱语”,大家可以跳过。我的话就四句,一是大家一定注意“新诗”(我近几年一直用“新汉诗”这一称呼)的文体形式问题,它所关涉到的“意、气、象”我多有论述,特别是关于“气”在新诗文体形式中的作用,是对声音诗学、视觉诗学等的进一步梳理和挖掘;二是永远不要偏离了新诗写作的一条原则,那就是“灵性”和“想象力”,人们说诗是人类得以求真向善的最后的城堡,我想有它的道理,西方式理性和科学只有在保有人类“灵性”和“想象力”前提下才是理性和科学的;三是要有对汉语的敬畏感和责任感,母语承载了我们祖先的创造,我们的文明是人类“轴心期”产生并延续下来的,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智慧,就像诗,诗意是亘古如斯的,看谁能凝聚一个时代最厚重的诗意,现代人未必在诗意书写上高于古人;四是一个诗人首先要做好一个“公民”(当然我们要先去争取),要像上帝一样思考,但必须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提高自身的和诗的境界。为此,诗人要敢于承担苦难,如果这些苦难必须由我们来承担的话。关于境界问题,洛夫先生在谈到诗的四个层次时也是这样讲的,我在这里不过是再说一遍。
综上所述,我对“90后”的概念是存疑的,对“90后”的作品是充满期待的。临近结尾,我忽然想到诗友岩峰的一首旧作《夜吟》:“我躺在柔软的麦田里/沐浴着春风/天上的星星时隐时现/像渔船/在大海里航行/那白色的云朵/或许 是船头激起的浪花/我想一定是离得太远/才听不到一点响声”,这首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作品,你也可能认为它本质上不是诗,但它仍然让我怀念,是因为它的纯净、悠然和无忧无虑的生命气息。他那时不足20岁,正像现在的“90后”。你们的作品肯定是整体进步了,但诗意却是可以超越时间的,因为那里有真诚、真情!
是的,“情感”诗学,一如我给桑恒昌先生所写的,它也许只是写作的一个维度,“感动”却是全人类艺术的母语。面对悄然站起的诗坛新生林,我拉杂地写下上面的话,以表达我的祝贺、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