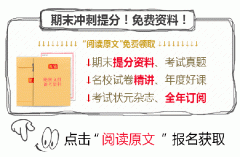2017年1期《散文选刊》(上半月选刊版)抢先看
2017年1期《散文选刊》(上半月选刊版)抢先看 (2016-12-29 11:09:52)
观点 钟声传来,我们被惊醒
⊙吕 新
尽管很多时候肚子里空得咕咕地响,可仍然会去关心一些与吃饱无关的寡淡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外国人存在,却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知道一些国家的名字,但同样不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这事有一半以上相当于一个传说或谣言。对于我来说,只有位于我们北边的苏联,才算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比较真实的国家。
十二三岁之前,我以为外国人的身体构造和我们有不一样的地方,尤其是他们的两条腿,以为他们没有膝盖,不能弯曲,永远是直的。
十岁之前,我以为外国没有白天,尤其是一些所谓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永远是黑夜。没有植物,有花也是黑色的花。黑暗的街上污水横流,水里跑着老鼠,到处都是血和尸体,天色比《雾都孤儿》里的天色还要更黑暗一些。
这样的一种印象或见识,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于客观世界的作用,书上图片上的外国人,就是那种感觉没有膝盖,腿永远不能弯曲的人。甚至觉得他们裤子或者大衣里面的腿不是由骨肉组成的,而是一种介于钢铁和塑料之间的材料。曾经问一个成年人,外国人能不能像我们一样把腿盘起来?他说,真能瞎想,那哪能盘,一盘就断了。
说的人轻松、平淡,听的人却无比惊心,还有一种替别人疼痛的感觉,耳边似乎还伴随着嘎巴嘎巴的断裂声。
看过一本法国人和越南人打仗的小人书,有一页是一个法国指挥官的后脑勺,感觉他的后面不是正常的头发,而是由岩石和石灰、麦秸组成的一片乱七八糟的东西,顿时就觉得法国人很可怕。很像是扑克牌里从j到k的那几个人。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边打牌,一边讨论他们是不是人,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意见从来没有统一过。
看到画像上的那些大胡子的外国人,经常杞人忧天,替古人担忧,想他们吃饭或者喝水的时候,得专门腾出一只手,把胡子撩起来,然后把东西放进去。想他们吃馅饼或油饼的时候,一定会有油流到胡子上。吃完饭,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洗脸,洗胡子。
春天或冬天的夜里,听人讲故事,知道薛仁贵的主要对手是一个叫盖苏文的朝鲜人。讲故事的人说盖苏文,黄头发,绿眼睛,粉红色的脸。故事继续往下进行,我却停留在盖苏文的相貌问题上。黄头发,绿眼睛,粉红色的脸,我在想,一个朝鲜人,怎么能长成那样。有很长一个时期,我把盖苏文的相貌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相貌重叠起来,很多年后见到后者的照片,发现完全不是,并在心里惊呼,这不是东六台的吴守文么?他更像是一个离我们不远的人,尤其像极了我认识的一个叫吴守文的人,比吴守文实际的兄弟更像他兄弟。
我们想象外国人每天怎样睡觉,一定是直挺挺地倒下,再直挺挺地起来。在张宝他们家里做过试验,发现腿要是不能弯曲,人很难让自己躺下或者起来。要躺下,就只能把自己朝前或者朝后摔倒,不摔倒就无法躺下。至于起来,就更困难了,没有人帮助,几乎就不可能起来。这就是说,一个人每天要起来,必须得有人帮助,可是,谁又是第一个起来的人呢,他难道不睡觉?既然他也要睡,那又是谁把他扶起来的呢?这个问题让人非常头疼。可就在那时候,我们中间年龄最大的王焕珍突然又提出一个更让人麻烦无比的问题:家里人多还好说,要是家里只有一个人呢?那怎么睡?王焕珍的意思是那将面临着躺下去起不来的危险。
最终,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如果家里只有一个人,那就只能站着睡,把头趴在柜子上迷糊一会儿,因为你已没有资格和条件躺着睡。
张宝的爹是一个铁匠,平时打的最多的东西就是马掌和锄头。那天他没有去铁匠炉,在家里用绳子串马掌。听到我们的议论,在一旁说,闹了半天,洋人们活得也麻烦呢,还不如咱们呢。咱们吃好吃赖先不说,最起码能自由活动,想躺就能躺,想起就能起来,不用人扶。
洋人!是的,那时候我们周围的人们管外国人不叫外国人,就叫洋人。与这个词相关的还有一连串兄弟般的词:洋火,洋布,洋灰,洋烟,镐叫洋镐,大号的铁锹叫大洋锹,高大的马叫大洋马,自行车叫洋车,搪瓷叫洋瓷。有一些更加苦寒的地方,甚至把白面叫做洋面。而洋葱,却多少年来一直被我们叫做葱头,直至现在,直至将来。
我曾经问过一个喜欢鼓捣无线电的人,是我小学同学的哥哥,我问他外国人里面有没有罗圈腿。他很肯定地说,肯定没有,他们那种腿,能断了,也罗圈不了。你能让一双筷子罗圈了么?
好像是高尔基还是谁,有一个故事里面有一个罗圈腿的人,我看了以后惊呆了。谁说外国人里面没有罗圈腿?从那以后,我开始怀疑以前听到过的很多东西。
人,很多的所谓的见识或者知识,其实只不过是一些谬误和谣传。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人,看上去踌躇满志,肚子也圆滚滚的,其实里面装着的基本都是废物。
我不记得第一次看外国故事是什么时候,现在能想起来的就是几本小人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可能不叫钢铁,就叫《保尔·柯察金》,还有高尔基的童年三部曲。高尔基的书是中学时候开始看的,此前看的都是小人书,印象极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只看过小人书,所有的记忆也都停留在那两本小书里,真正的书从未见过。
这两位的小人书,让我认识了苏联的小孩,他们脸上长着雀斑,头发是亚麻色的,至于亚麻色是什么色,则完全不知道,感觉就是白头发。我周围没有白头发的小孩,只有脸上有雀斑的,住在我们隔壁的与我同龄的广昌就是一个脸上有雀斑的孩子。
外出上学以后,图书馆取代了昔日的那些伙伴们,我开始读那些历史的清单。借阅的第一本书好像就是《忏悔录》,却读得很夹生,看完了也不知道到底在忏悔什么……这中间,读得最混乱的就是《悲惨世界》,好像是四本,感觉如临大海,人完全被淹没在其中,不得不把一些段落抄录下来。我用省下来的钱自己买过《少年维特之烦恼》《双城记》和《死屋手记》,与《死屋手记》同时买的还有同一作者的另一本很薄的书,忘了叫什么。
曾经亲手抄录过从图书馆借回来的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还有一本波兰的民间史诗,好像叫什么瓦,现在全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