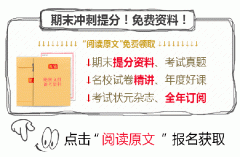2017年1期《散文选刊》(上半月选刊版)抢先看(2)
八十年代中期,因为出差,曾经在一个月内两次光顾同一家县城的新华书店,两次都有所获,买到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两本书。第一次买到了《喧哗与骚动》,第二次买到了《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都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两本书。
这么多年,看书一直都是躺着看。在我迄今为止的阅读生涯中,那本黄皮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是我唯一的一次使用红蓝铅笔,在上面留有标记,画过红线、蓝线,只是因为有太多的感觉。很多年以后又买过三卷本的文集,却好像没怎么看。
九十年代初,跟随一群人去过一家译文出版社,还去了他们卖书的地方,却一本也没有买。这事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天天买肉,等真正到了屠宰场,参观完以后,却一斤也没有买。
人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奇怪最难琢磨的一种东西。
一位曾经在国营书店工作过的朋友领我去他们书店的库房,我在灰尘里发现了那本0.79元的《胡安·鲁尔弗中短篇小说集》。迄今为止,我也只有这一本。
谁能以十万字成为杰出的伟大作家?全世界只有这个孤独无援的来自贫穷乡村的墨西哥人做到了。
很多人动不动就炫耀自己著作等身,写了多少多少,却从来不提他前前后后糟蹋了多少纸。美丽的纸,洁净的纸,一旦印刷了那些垃圾文字,也即刻沦为废品,只能以公斤论价。
九十年代初,在阴雨蒙蒙的巫山县,我们从新华书店买书出来,然后在泥泞的街上吃饭,吃巫山县的饺子和素炒白菜。晚上七点多,步行到码头,船舱里的灯光像火车上的灯光。就在那种不太明亮的灯光下,翻阅着上面盖有“巫山县新华书店”戳印的《洪堡的礼物》《兔子,跑吧》《白鲸》,何等的快乐。贝娄至今仍是我喜欢的作家。《白鲸》则越读越感觉像儿童文学。
与我同行的是两位河南兄长,田中禾,张宇,他俩一路上照顾着我,我们的友谊也就此缔结。时至今日,无论何时何地相见,都会无比亲切。在我来说,感觉已不再仅仅是友情,而是一种亲情。
人世间,存在着这样一种情感,总有那么一些人,无论同性还是异性,即使一百年不见,也永远不会生分。
2000年之后,读小说的数量和耐心明显下降,只选择少数自己有兴趣的看一下。我早已不在意别人使用了什么手法或者何种形式,在意的是书里写了什么。
与很多丑陋的叠印出作者利欲嘴脸的文字相比,我更愿意看一些传记,日记,以及书信。
别的我在这里先不说,只想说说冻土带上的一些事。
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夜深人静的时候,合上书,就像从海面上升起来的一样,眼前慢慢地会浮现出金黄或银白的六个字:借钱,或者预支稿酬。六个字蹦上蹦下。
这个人写作,通常不是以字数计算,而是以印张来计算。“今天又写了一个半印张。”根据这一个半印张,很快就能计算出可以得到多少钱。再加上此前已经写出的七个印张,他心里已有了数。“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请汇二百卢布给我,我有急用……”
尽是些这种信。
有时候,为了能尽快得到钱,会把对方猛烈地夸奖一番,用上“世界上”“全世界”“最慷慨,最善良”等等的字眼。
二百卢布到手,就会升起相关的梦想或者幻想,拿它去碰碰运气,谁又能保证一个小时以后它不会变成一千甚至两千,完全有可能。轮盘面前人人平等,凭什么别人能够满意而归,他就不能?上帝总是为他这样的人设置一些难以逾越的壕沟,壕沟里有模糊的脸在看着他,他不得不一次一次地跳过去。两千卢布?能做不少事呢。于是就去轮盘前坐下,忽略任何一张脸,只注意前面的颜色,那即是世界的颜色。轮盘优美地转着,转啊转,就像流逝的时间,别人的一杯咖啡还没有喝完,他刚到手的二百卢布就被永远地转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有时候我想,如果他不贫穷,如果他也像托尔斯泰或者屠格涅夫一样富有、健康,也是衣食无忧,是否还会写出他的那些作品?或许写不出?或许更好?或许很差?这种事无法假设,对于一个具体的人而言,尤其如此,因为一个人在这个世上只能活一次,只能沿着属于自己命运的小路走下去。我相信命运的专属性,一个人只能怀抱或者披挂着属于他本人的那些东西混世界,其余的迟早都会脱落或丢失。尽管后来的人们还在读他的书,还在研究他,甚至说他还活着,但是对于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来说,他确实早已死了,因为他的颜面不再抽搐,胃也永远不再感到饥饿。与此同时,他也一起埋葬了生前一直对他纠缠不休的贫穷和种种屈辱以及忧思。
……
再看托尔斯泰的书信,从来不谈钱物,全部都是对于形而上的表述,宗教、社会、哲学、教育、人生、艺术、道德、救赎。
钱对于前面的那个人来说很重要,但是对于后面的这个人,却如粪土。
尽管他本人不吃肉,每天扛着枪出去打猎,但后面的这个人本身却像一块散发着强烈气味的肉,每天都会招来那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圣方济各会会员、天主教徒、青年教师、龙骑兵军官、文学爱好者、教育改良者、身无分文者、肺病或结核病患者,还有大量身份不明的面目模糊者。托尔斯泰有时单独与某一个人面谈,还有的时候把他们召集起来一锅烩,谈话中既有制度建设,又有宗教改良,当然还少不了艺术与教育。作为女主人的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简直要被烦死了,家里永远住着生面孔,餐桌前永远坐着数量不等的不认识的人。
她记日记已有半个世纪,所记均为她本人所见所想。就像一个故事,由几个不同的人分别讲述,每个人讲的只是自己看到的那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索菲娅能看到的东西已越来越少,家里很多事情都瞒着她,她只能看到事情的一长条或者一个角落,一件事情的三分之一甚至六分之一,另外的那些部分都对她遮蔽着。托尔斯泰出走的第二天,她还像平时一样去叫他吃饭,却没有人在,她找遍了整个亚斯那亚·波良纳,也没有他的人影。
她想着,或许应该再去为他重抄一遍《克莱采奏鸣曲》,或者《哈泽·穆拉特》。
也有欢乐。她和女儿们朗诵俄国某个作家的一篇拙劣的短篇小说,边读边哈哈大笑,托尔斯泰正在和别人下棋。索菲娅写到:听到我们朗读,听到我们哈哈大笑,列夫也笑了。
一九一八年,列宁下令,由苏维埃政府每年提供给列夫·托尔斯泰的遗孀八千卢布。
孤独的老太太在日记里郑重地记下了这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