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选刊》(上半月选刊版)2017年3期抢先看(3)
来源:网络转载 2017-03-26 11:29
编辑: www.xigushan.com 查看: 次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深陷这种矛盾纠葛之中,我的泪腺已经干涸了,真可惜,再没有悲伤的事情能使我俯下身来,找不到出路。而拒绝哭泣好像是因为眼泪抢走了原本就属于我的角色,晴的时间太久,真想没有缘由地掉上几滴眼泪,借以证明我体内的盐还没有完全逃出去。
起初,在被刺伤的那些日子里,我躺在医院病床上,如同一具刚刚出土的兵马俑,长久一动不动,心里却莫名轻松。甚至,依稀记得朋友扶着我奔赴医院时的焦急与慌乱,我捂住胸口,脚步摇曳,喘不过气,咧着嘴,想笑。司机惊讶我满身的鲜血,泪痕一样,斑驳,刺目,最终紧闭车门扬长而去。拒载!他一定是害怕我在他的车里画上句号,或是担心我鲜红的泪水会打湿他散发着浓烈羊膻味的坐垫。该死,我一定是吓住他了!可笑的是,在手术推车上,我迷迷糊糊,居然拿出饭卡让医生去支付药费,“肇事者”一脸严肃地说:“放心,我闯的祸,我负责。”如果要召开一场表彰大会的话,我一定会说:感谢那些流离失所的鲜血,替我流泪、替我排毒;感谢死亡线,以及那把光滑锃亮的剪刀;感谢痛,把我从混沌中救出来。后来司空见惯,轮椅、白大褂、药水味、手术刀……人,那么的脆弱无力。每天,我跟随着他们,提着一根从身体里蹿出来的引流管,排着长队,在狭长的走廊里来来回回,就像一群丧尸,着装统一,步伐佝偻。自此,好多隐蔽性的东西向我迎面扑来,在这特定的地方,我们不分彼此,小心翼翼挪动着碎步,双手守护着层层包裹的伤口,而那些痛,得以被我们的专注放大,显得无比谨慎、暴戾。真想弄清楚,为什么我们活得如此相似,却会痛得因人而异呢,看来疾病面前也未必人人平等。我们只是欠自己一个难以言表的说辞罢了。
其实很想问一句:你有多久没流过眼泪了?
先别着急,卸下盔甲后,仔细想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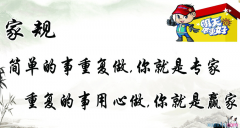
![《聆听名家诵读精美散文》[MP3]](http://www.xigushan.com/uploads/allimg/170127/051HV347_lit.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