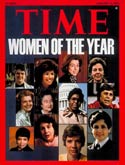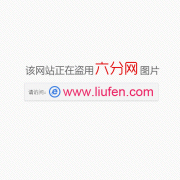张太原:大历史脉络中的人物关系
张太原:大历史脉络中的人物关系——周恩来与胡适
作者: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3年第6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年05月20日
摘要:周恩来与胡适都属于中国20世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走的道路不同:一个是革命领袖,一个是“改良主义者”。纵观二人的关系,五四时期是一个交合点,共同推动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然而不久二人却逐渐疏离,走上了不同的社会改造道路。大约到1937年前后,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二人的关系又出现了一个交合点,一个是政党的代表和领袖人物,一个是知识界的代表和知名人物,一起研究救国方略,体现了在政治和抗日方面的某种共识。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看来,胡适属于“典型资产阶级思想”和“唯心主义”的代表,在无产阶级政权中是需要批判的,但仍希望其“为社会主义服务”,并设想给其一定的言论空间。而对于胡适来说,他根本不认同中共新政权,对周恩来的好意自然无从回应。二人的名字和关系,可昭示“大历史”发展的脉络。
关键词:周恩来 胡适 中国共产党 历史轨迹
人物研究走到一定程度,常常会出现选题的困难,尤其是像周恩来这样的历史人物。但是,如果把人物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研究路径,就可以由微观通向宏观,使人物与时代相连,与社会相依,不但可以呈现时间之流程,而且可以展现空间之构成,并可使历史的静态与动态融为一体。这一研究取向下的人物,就像一只多彩笔,用它可以绘制立体的动态图景;又好比一扇窗,凭它可以开启风光无限的新视野。这样以人物为路径重建的历史会更直观,也更贴近历史的本来面目。按此,一些看起来不相干的人物,可能隐藏着某种历史的联系。比如周恩来与胡适,二人都属于中国20世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走的道路不同:一个是革命领袖,一个是“改良主义者”。尽管反映他们直接关系的材料很少,但是通过一些零星的碎片,却可以昭示“大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一、敬爱与失望
五四前期,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周恩来则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学生。1918年2月,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仍津津有味地阅读已在国内看过的《新青年》杂志,对其中倡导的排孔、独身、文学革命等表示“极端的赞成”。1919年7月,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更是以介绍“新思潮”为主要旨趣。稍后,他还主持成立了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研究的觉悟社,并邀请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前去讲演。①这期间,虽然没有材料显示周恩来与胡适的直接联系,但是,对周恩来来说,胡适当是他所熟知的新潮人物。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五四时期,陈独秀和胡适代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了他心中的楷模。②这差不多是那个时代青年思想变化的一种普遍轨迹,周恩来显然也在此列。1922年12月,他在专门评胡适的一篇文章中开篇即说:“胡适先生本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和言论很有些令我们佩服的地方。”③不过,一个“本”字表明,大概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这种“敬爱”和“佩服”已成为历史,而此时却是要批判胡适。
相当一段时期内,思想史著作中一般都把“问题与主义”之争看作是新思潮阵营分裂的标志,由此断定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分道扬镳。现在的研究表明,这未免有些受后来历史结局的影响。如果循着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去考察,则会发现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并不是一下子就截然分明的,而是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似分又合的胶着状态;两者好像是为着同一个目标而采取不同方法努力的朋友关系,“我们”中往往有“你们”,而“你们”中也常常有“我们”;大约到1925年以后才分出两个阵营、两条道路。④这期间,胡适更倾向于“求同”,特别是“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论政”,“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与苏俄和中共走得也相当近。“胡适踏足政坛,虽以《努力》为根据,真正涉及时政大事,似乎更加喜欢与李大钊交换意见。”⑤
各种材料表明,“问题与主义”之争,并没有影响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1922年,胡适起草了一个政治宣言即《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中说:“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⑥该文公开发表时,胡适征集了16人签名,其中就包括李大钊。虽然对于李大钊来说可能有碍于情面或实施策略的因素,但是双方在大目标上的某种一致也确实存在,至少说明当时个别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完全放弃“和平的努力”。或者可以说,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界线这时虽然有所显露,但是缘于先前的友谊、交往和同道,在一些重大举措上彼此仍然“相互捧场”。比如,中共二大宣言发表后,胡适即撰文予以“正面的响应”,称“中国共产党近来发出一个宣言,大意是说他们现在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胡适还明确地称中国共产党为“我们的朋友”,并且在大目标上引为同道。⑦
1923年和1924年,陈独秀曾多次致信胡适,请他帮助蔡和森出书和索取稿费及帮助张申府推荐工作,同时还替《中国青年》向他约稿⑧,并允诺为胡适筹办的《努力月刊》“义务撰稿”⑨。1923年7月,瞿秋白在致胡适的信中,表示希望所任教的上海大学“能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请胡适常常指教。⑩同年,陈独秀在《前锋》上撰文,说胡适是“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认为唯物史观派和实验主义派“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11)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对逐渐被看作“改良主义者”的胡适等人的态度并不一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办的《少年》杂志中,就指斥胡适等“知识阶级的人”,“历来是资本阶级的附庸”,而“我们”即“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是劳动阶级的先驱”。(12)“资本阶级的附庸”和“劳动阶级的先驱”显然是对立的两个阵营。蔡和森则指责胡适等“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治家或政论家”,“简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有群众的势力,所以他们不谋勾结或利用旧势力便想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不是发表些蔑视群众,谩骂工人兵士的怪议论,便是想出些上不靠军阀下不靠民众的智识者的纸老虎或乌托邦”。(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