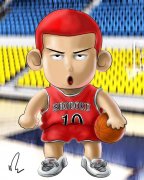“九·一三”事件人物张逸民(4)
“别看我60多了,全身零件从大到小没一点毛病哩。”老人不无几分自豪地笑道。每天坚持跑、跳、单双杠、门球等体育锻炼,是老人当海军后养成的习惯,几十年风雨无阻,乐此不疲。老人健康乐观,我自然高兴。但温热的高兴中也掺入了些许寒凉的感伤。如果有人告诉你,眼前这位体力精力旺盛、对国家有过很大贡献的人已整20几年没有工作了,像一台状态良好的设备,被长久地锁在仓库里形同废铁,默默地锈蚀氧化,你会作何想?
我用眼下颇为时髦的方式提问:您一生最得意的事?
当海军,打掉了三条半。
您一生最糟心的事?
下半辈子没为海军做任何贡献,光领俸禄不出力,心里有愧啊。
您现在最想干的事?
为海军再做点什么,做什么都行。
我是1946年7月在东北参的军,四野六纵,43军。在团部当过书记,师部当过作战参谋,参加过打长春、四平、辽阳、鞍山,辽西会战,然后入关,一直打到海南岛。全国解放,建设海军,从陆军中选人。我当时算有点文化的,首长都不愿放我。但我心里乐意当海军,因为打海南渡海时吃了敌人军舰的亏,我们的木船被狗日的军舰打沉了好几条,那时就想,我坐的如果也是兵舰,一定好好治治那些王八蛋。在苏联,敢上鱼雷艇的就算半个英雄,因为鱼雷艇被比喻是“海上爆破手”,“海上送炸药包的”,近距作战,危险性很大。我说,我愿到青岛三海校学鱼雷,危险我不怕,只要有仗打,能到第一线。三海校,我是同期中第一个放的单航,比一般人少一半时间。苏联顾问挺看得起我,说,“达哇立士”张(张同志),在苏联,你能得很多很多卢布。他们那儿,节约了航油,可以折成钞票奖给个人。毕业后第一次参加海战是1955年1月10日晚上在东海打“洞庭” 号。现在回想,当时年轻,胆子也确实大,暗夜、浪高,我又是单艇独雷,换个人真不一定敢走,我楞是带一条艇闯出去了。天寒地冻,那个冷啊,别提了,甲板上冻了手指厚的一层冰,滑得不能走人,12.7机枪管,结满了冰,月光下像两根白蜡一样。我胸前系一条围巾,也冻成冰疙瘩了。海浪迎面打来,海水从脖领灌进去,一直冷到臀部、小便、两腿根,回来后,脚面冻得像个馒头。好在月亮刚出来,能见度不错,老远就看到了“洞庭”号的影子,我悄悄靠近它,也就是一链的距离,亲自扳的发射把,打在它的当中。这是一条美国造,密封好,6小时以后它才沉没。后来我们潜水员下去看,在海底它断成了两截,不在一处。一条雷就要了几百吨的“洞庭”号一条命,我觉得干鱼雷艇是干对了,再苦再累再冷心里也高兴。而且,有了头一回胜仗,以后出海,心里不打怵了。
1958年8月23日傍晚,盼了好久的炮击开始了,我们看不到听得到,天边轰轰轰打闷雷一样,无数很重的声音重叠在一起。对我们鱼雷兵来讲,好比战鼓擂得心里很痒痒,还没接到出击命令哩,我就让各艇开始暖机。鱼雷艇的发动机和喷气战斗机是一样的,润滑油必须加温到43’,才能跑高速。个人的、参战艇的决心书、保证书送到我这里一大摞,同志们的口号是“大炮欢迎,鱼雷送行”,准备和国民党海军拉开架式大干一场。帮我们伪装的船老大看到我们要出去打仗都流泪,一个老汉伸出大拇指说,解放军不简单,我活了六十几岁,还没看过军队打仗这么高高兴兴的哩,像跟去看大戏一样。结果23日我们没打成,24日傍晚接到副支队长刘建廷的命令,说敌人逃跑了,立即出击。我马上把各艇长叫到我的指挥艇上,作一次战前交待,其实讲的很简单,中心思想几句话,要保证做到“三不放”。第一,距离不到不放,进入三链500米以内再发射,谁打早了放跑了敌人,回来算账。第二,角度不好不能打,敌向角,即我们攻击方向和敌航向构成的角度,要呈扇面状,必须大于45°,小于100°。第三,战斗状态不稳不能发射,艇身不能左右摇摆,要很稳很稳才成。我们一共出动了6条艇,一中队的184、175、103号和二中队的180、105、178号。184号为指挥艇,180号为预备指挥艇。我在184号上,跑在最前边。鱼雷艇打仗和骑兵打仗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冲锋时,首长在前自身引导带队冲,如果我被打掉,预备指挥艇马上自动接替指挥。所以,干鱼雷艇指挥员最基本的要求是不怕死,而且死的可能性也确实比较大,谁叫你爱上这一行呢,那没有办法。18时10分,我们以单纵队出击接敌。记得太阳离落山还有好大一截哩,海面微风小浪,能见度大于5海里,是一个适宜鱼雷艇攻击的好天侯。但一出海就遇到了麻烦,我还没有开足马力,其它5条艇都掉了队,耳机里有人喊“加速加不上!”我就叫184号也加速试一试,果然,一挂高速档发动机就冒黑烟,艇速却上不去,像一台在泥地里往前拱的拖拉机。用不着检查,我知道是海蛎子在捣乱。你大概也知道吧,鱼雷艇跑高速,艇底部必须保持光滑清洁,最大限度减少海水的阻力,这同滑雪板越光滑越好的道理是一样的。一般鱼雷艇只要三天不出海,艇底就会长满密密麻麻黄豆粒大小的海蛎子,正常情况下,清除很容易,我带着艇队到海上跑一圈最高速,等于每秒二十几米流速的海水就把还没长结实的海蛎子全部冲刷掉了。每次总参、海军来检查装备,我的艇都是保养最好的。这一回不行喽,在厦门不挪窝隐蔽待命20多天,艇底的海蛎子全长到墨水瓶盖那么大,趴得死死的,战士们怕到时候艇跑不动,每天轮换潜到艇底用刮锈板刮,脊背、胳膊腿被海蛎子壳割出一道道伤痕流血不止仍坚持干,管点用吧,但已不可能彻底弄干净了。我也是头一回领教,海蛎子这玩艺真他妈讨厌,平常训练我敢开到55节,现在只能开到27至28节。鱼雷艇的优长就是一个高速嘛,速度上不去,对“八二四”海战的影响简直太大了!出了定台湾,艇队90°左转弯,我就彻底亮相了。航路上,有一个敌占的小岛——东碇岛,大太阳底下,我知道是要硬闯这一关的。果然,在距离4.5至5海里时,东碇敌人开炮了。小高炮、速射炮打得挺欢,炮弹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炸开。紧接着,我们的岸炮开始压制射,炮弹弹道低得不能再低,就贴着我们头顶划过,声音很响,像鸽子起飞,喀勒勒勒——,很快硝烟就把东碇岛完全遮盖住了,敌炮也哑了。现在回想,敌人方面的一个重大失策恐怕是通信不灵,如果这时候东碇立即把我艇队出动的情报报告其料罗湾舰队,我们突袭的计划大概会落空。而事实上,我们从东碇到料罗湾又走了近1小时,他的舰队仍然糊里糊余,可见敌人也乱了套了,他的情报是逐级上报的,机械、呆板,并且东碇到金门之间,金门到海上舰队之间,肯定哪个环节上传递不畅,导致贻误了战机。我虽然只有28节的航速,平均每秒钟也是10米啊,换一个角度讲,敌人的情报传递每延误1秒,就意味着危险向他的舰队迫近了10米,问题是,他整整延误了3500秒!其实,当时我不可能想那许多,鱼雷艇一旦出航就是离弦的箭,敌人发现也好不发现也好都是一码事了,我们不可能再缩回去,只有横下一条心,豁出命也要把鱼雷扛上去同他干!18时40分,我的雷达在左舷30°、距离130链处发现了从料罗湾外窜的敌舰群,我就讲:“黄河,发现目标,准备战斗”,再说两句鼓励话。我打仗,讲话很少,这次战斗,一共讲了不到30句,战后,总参通信兵部部长还专门表扬了我。平时训练,我很注意养成一种习惯一种作风,尽量少讲话,讲一句是一句。因为指挥员不管哪一级,讲话太多下面就疲塌了,你就没有威信了。我当参谋长、大队长,那可是绝对权威,老天下大雨,我说今天出海,没有人敢怀疑是不是出的去,都得给我撅屁股老老实实做准备。所谓权威,我理解,就是不讲废话,每一句话说出来都钉钉砸坑,很有分量。由于许多同志是第一次上战场,难免有点紧张,我又下令,“各艇唱歌”,目的是要大家安定松弛一下,在最佳状态中完成各种动作。说来挺有趣,我们6条艇是一边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一边向着敌人接近的。60链时,根据雷达报告的方位,我看到远处有一个灰黑的长条,开始模糊,逐渐清楚。继而又看到好多长条。按照比例,敌舰这时看我应该只是几个小黑点,我心里明白,他肯定还没有看到我。30链时,左前方突然出现两个小目标,是敌人两条小炮艇,航向与我并行。正值黄昏,西南方偏亮,东北方略暗,我恰在亮处,他看我应该更清楚。我着实紧张了一下,让各艇把烟幕弹准备好。但两条敌艇居然无任何反应,我估计,我们刚打完炮,敌人可能惊魂未定,注意力都在金门那边。另外,他们的小艇也不一定装备有雷达。我又侥幸过了一关。距敌4-5链时,敌人终于看到我了,打信号灯,一闪一闪和我联系。要打招呼早就同你打了,现在还联系个屁,恕我无礼啦,率领艇队一头就扎到敌舰堆里去了。进去没一分钟,敌人开炮,可惜晚了,“台生”、“中海”两条舰已经没地儿躲闪了。时间我记得很清楚,19时25分30秒,我率一中队三条艇在距“台生”号2-3链间以敌舷角70°左右的攻击扇面上占领了齐射阵位。也就是300米嘛,太近啦,我的整个视线里已全是敌人的这一条船了,敌水兵在甲板上乱作一团跑来跑去、敌舰首冲起的浪花看得清清爽爽。我喊了一声“打!”5条鱼雷嗖嗖嗖出去了,一共击中两枚,哪条艇打到的搞不清楚,我估计可能性还是我的184指挥艇大,因为我居中攻击,位置最好。打完,我们立即作180°转向、脱离。刚刚转过来,就感到艇身猛烈震动,回头,先看到一个大火球,有多大呢?整个“台生”的舷翼都成了一个大太阳,比船体还高出一块,红里透黄,光芒耀眼。紧接着水柱从海底深处直冲上天,水柱高度,能有船体的三、四个高,非常壮观。水柱下落后,一切浓浓的白烟又升起来了,这时候,肉眼已看不到敌舰,它完全被烟雾盖住了。接下来,可以听到烟幕中发生连续不断的爆炸;不到5分钟,雷达兵就报告,“台生”已从荧光屏上消失了。我打过的几次海仗,数这条敌舰沉得最快。“台生”是国民党的一条大型登陆舰,4000多吨吧,当运输船用,满载,又运上去一些伤兵,几百人总是有的。战后,我说,我作孽哟,两发鱼雷不知要了多少人的命,反正不可能有活的。几乎是同一时间,二中队三条艇向与“台生”一般大的“中海”发起攻击。严格讲,二中队的战斗动作未按要求做,不够沉着准确,急于求成,没有进行编队齐射,而是依次单艇轮流发射,大大降低了命中率,6条鱼雷仅命中1条,打在“中海”的尾部,动力全部摧毁了,虽重创,但未能击沉它。鱼雷艇就是这么个玩艺,两条雷放完,就成了没有任何威慑力的活靶子,战术动作只剩下一个,说好听点叫“撤”,说难听点是“逃”。我命令各艇释放烟雾,全速撤出战区。敌人炮舰上的速射炮下雨一样追着我们打。到了较安全海域,我叫雷达搜索观察,数来数去,一共撤出了五条。用电台呼叫,才知道175中弹负伤了。175回答,它还有一台发动机,可以自己回去。这时候天色已黑下来,海面上一片烟雾,敌人的炮越打越凶,收拢编队已不可能,岸上又一个劲催我们速撤,于是,我下令各艇自行返航。实际上, 175伤得很重,他报告“自己可以回去”是好意,怕连累了整个艇队。但不管怎么说,我没有拼死回去搭救是犯了一个难以宽容的错误,现在想起来,依然很难过,很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