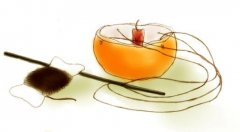《中国散文家》2016.6期“梦到了那个叫五里的地方”(3)
小学校生活之平静,是我所喜欢的。但无边无际的寂寞,又让我难捱。每天傍晚,我充满期盼地等待邮递员送来报纸和信件,查找有没有用稿通知和远方友人的来信。那段日子,是学生带给了我快乐,与天真的孩子们相处,我感受到真正的欢愉。孩子们并不太怕我,我也不希望他们怕我。我教他们读好的书、写童真童趣文字。我还给他们办了芦花文学社,编印《芦花》油印刊物,指导他们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近百篇童诗、作文。“芦花”的名字,是我起的,这是里下河水乡最常见的一种风景。
新学期排课表时,我将语文课排到第二节,那已是在9点以后了。每天早上,我从集镇长街的东首散步到西首,到谢三子早点店点上一笼蒸饺,就着醋慢慢品尝。谢三子做的蒸饺味道真是好,我现在还犹记余香。离开五里后,我就再也没有吃过比这更香的蒸饺了。
这样的生活过了6年,其间还经历了恋爱的挫折,渐渐地我已不再甘于孩子王的平静生活。后来,我不断往县城跑,拿着教书之余写的一点东西,找到刚刚创办的县报。老总对我有点印象,也正是用人之际,终于为我打开了逃离乡村的一道门。
逃离五里,至今仍认为是一种庆幸。尽管那里留下了我最美好的青春韶华,留下了人生中刻骨铭心的记忆。我的不少师范同学,至今仍在乡村从事这份平静细碎、令人尊敬的职业,面对他们的坚守,我感到惭愧。但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已不再如沈从文先生笔下的风景。从事新闻工作后,我走访了许许多多的乡村,对于中国乡村的现状,有着一份深刻而感性的认知。乡村,被城市化车轮碾过,渐渐被时代疏离、淡忘,与城市的日新月异相对比,差距愈加明显。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必然,也是历史的无奈。或许数十年后,当中国乡村不再凋弊与失落,我们这个社会就会掀开新的一页。
关注乡村,关注乡村无数的父老乡亲,不能只是人文学者的笔下情怀。中国各级政府的主政者们,更需要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乡村,把美丽乡村建设的精髓细细地落实。
逃离乡村的我,是不会真正逃离乡村的记忆的。五里,这个生我养我的土地,永远是我的根,我的胎记,我的切肤之爱。
行走在故乡的土地上
◎ 丁尚明
丁尚明,山东东阿人,从军24载,2006年转业地方工作。在部队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曾三次荣立三等功。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山东文学》《前卫文学》《散文选刊》《华夏散文》《中国散文家》《当代散文》《散文时代》《东方散文》《湖南散文》《朔风》等报刊发表过数百篇文学作品。出版报告文学集《人间正道》,系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山东作家协会会员。
多少次梦中把你回望,多少次为你泪湿衣裳。自从没了爹娘,我把你唤做故乡。从此,你成了我灵魂深处最柔弱的地方。我曾把你束之高阁,也曾把你尘封心上,如水的日子里,我对你的思念如山高水长……故乡啊,故乡,你是我的根,你是我的魂,你是我的生命呀,我永远是你牵挂的儿郎。故乡,我何时回到你的身旁?
——写给亲爱的故乡
一
春天的花香刚刚散尽,转眼迎来了夏至。这时侯,大地一片葱茏,老实了一冬的河流,再也按捺不住火爆的性子,像脱缰的小马驹,在广袤的大地上,肆意地撒起了欢儿。
这时,弟弟的来电说,侄儿这几天就要订婚,问我能否回去。想来,自爹娘故去的六七年间,我回去的次数屈指可数。如今,家中唯一的侄儿订婚,我这个作大爷的没有不回的道理。再说,人过中年,总爱怀旧,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也就愈发地强烈。我是该回去看看了!
头天,给车充了气加满油,把烧给爹娘的纸钱,给亲戚、姐弟的礼物装上车。次日,天刚一放亮,我便驱车踏上归途。记得,前些年每次回家,我总把车上的音响开得山响,心欢神悦的我,有时竟随着音乐哼起小曲。那时,总感觉车速太慢,路途太长,真恨不得身上长出翅膀,扑闪就落到自家的院里。而此刻,同样行驶在那条回家的路上,心里却充满五味杂陈。
大约过了四个小时,我驶离了那座飞架东西的平阴黄河大桥。从桥头西往南一拐,便是曲曲弯弯的黄河大堤。我知道,再行二十来里,就是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了。行驶在走了无数遍的大堤上,我不由地放松了油门。我把车窗放到最低,大堤两边的风景顿时一览无余。这时,恰逢枯水期的黄河,已不见了那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的模样,那裸露在阳光下的大片洁白河床,就像卸下婚纱的新娘,正羞怯地躲避款款而来的新郎。那一弯缓缓流淌的浊流,莫不是新娘流出的幸福眼泪?
大堤西边,新淤积的坡坝上,遍布着挂满青果的核桃树和顶上打了荚的油牡丹。远处,望不到尽头的麦田里已泛起微黄。眼前的这一切,对我是那样的熟悉,又显得那样陌生。蓦地,前方不远处的水泥杆上,一块标有“丁口堤段”的提示牌,使我下意识地停了下来。由此,连接大堤的是一条被白杨林遮掩的狭窄的沙土路,密匝匝的树冠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到远方,辨不清方向,但我的心告诉说,白杨林那边就是故乡,那里埋葬着我的爹娘,那里是我从军离家的地方!
二
“哥,你歇会再去吧。”“我不累,先去坟上给爹娘烧纸吧。”
“那咱开车去?”“我想路上走走,我想看看四周风景。”弟弟拗不过我,我顾不上旅途劳顿,于是,提起纸钱,兄弟俩向着爹娘的坟头走去。
临街的石墙上爬满青藤,路上依旧是粹石嶙峋。村子里静极了,一幢幢院落破败荒芜,一间间老屋不见人烟。走了许久,总算遇到了几个熟悉的乡亲。故人相见,自是亲热。我一边寒暄,一边将准备好的“中华”烟递给他们。尽管我从不抽烟,只要回归故里,我总是提前备下几盒烟。走在大街上,逢人递上一支,已是我多年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