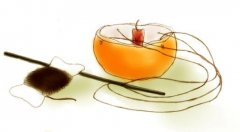《中国散文家》2016.6期“梦到了那个叫五里的地方”(5)
我身上流着黄河水一样的血液,我有着黄河沙一样的肌肤,我的生命里注入了浩浩黄河的魂魄。无论过去多少年,无论路途多遥远,故乡的黄河水呀,永远流在我心上,永远流在我的孩子身上。也正因此,自从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黄河便成了我写不完的主题。我参军不久,发表在济南军区《前卫报》,并荣获“庆祝建国35周年‘我们连队好’”征文大奖的处女作,便是《黄河一样的性格》。之后,我又创作并发表了《澎湃在心中的大黄河》、《记住,那条河》、《黄河杨柳青》等许多关于黄河的作品。别离故乡的几十载,只要回到故乡,我总要到黄河边走一走看一看,这次更不例外。
清晨,小山村寂静如斯,人们还在沉睡,我便向着黄河走去。朝雾氤氲的田野上,草尖上的露珠很快把我的鞋子、裤管打湿,传遍全身的丝丝凉意令我神清气爽。空中传来的一声接一声的布谷声,显得幽深而苍凉,而那些早起的鸟儿,则在密匝匝的树叶间齐奏起迎晨曲,叽叽喳喳,没完没了。久居城市的厅堂楼舍,行走在故乡的土地上,真有一种恍如隔世、误入桃源的感觉!
跨过黄河大堤,几步就到了黄河边。眼前的黄河异常安静,好似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我寻不见儿时黄河浪里的白帆点点,听不见黄河岸边船工拉纤唱起的号声阵阵,也看不到往昔黄河那气势如虹、浊浪排空的身影,我不免有些黯然伤神了。
踯躅在黄河边,凝视着那一泓清流,远眺着河对岸那绵延不尽的山峦,我捡拾着那些曾经的记忆。爹是船工,我曾无数次目送着爹的大帆船,在洪流中劈浪远去;每到夏天,我们一帮光腚猴儿跳到河里打起水仗,在清凉的黄河水里我们送走了炎炎盛夏;在黄河岸边的责任田里,爹带着我和姐姐们一走春种秋播;爹去世前几天,我在黄河岸边的杨柳树下,为他拍下了生前最后一张照片。如今,粗大的杨柳树依旧枝繁叶茂、树影婆娑,而爹已经化为一抔黄土……
我沿着河边行走,不经意间,水流处的一张粘网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好奇地蹲下身,轻轻地把粘网拉起,网中几只鱼儿正在拚命地挣扎。这让我动了恻隐之心,赶紧把鱼儿从网上摘出丢入河中。然后,又将粘网抛到一边。看着鱼儿悠悠地游走,我对下网人的歉意也烟消云散,反正,我心里是快乐的。
故乡枯水期的黄河,风平浪静,没有了惊涛骇浪。在初临黄河的人看来,的确逊色不少。我想说,可不能被眼前的假象迷住眼睛。黄河就是黄河,它的枯水期毕竟是短暂的,它在地球上已存活了115万年、流经华夏九个省(自治区),不管潮起潮落,它总是以磅礴的气势奔向大海。其实,人也应该像黄河一样,只要痴心不改,胸怀志向,人生路上管它峰回路转,终会到达理想的彼岸,实现人生的目标。
得知我回到故乡,战友杨晓锋特意备下酒宴迎接我,我刚入伍时的老班长赵成香闻讯专程从外地赶来。我还见到了沈刚、孙兴乐、王鲁林、麻荣军、马庆领、刘相福、李勇等,这些分别三十多年的老乡战友,如我一样都是鬓染霜华、年愈五旬的长者了。岁月无痕,战友情深。百感交集,无以言表。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任泪水肆意地流淌。
不沾烟酒的我,这次竟与战友们开怀畅饮起来。我喝的酩酊大醉,但我头脑依然清醒,我好想唱支歌:又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飘流在外头。愁更愁情更忧,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亲人和朋友,举起杯倒满酒,饮尽这乡愁,醉倒在家门口……
山里洪家,我童年的记忆
◎ 汪向东
汪向东,江西省上饶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1986年开始文学创作。获全国散文论坛征文赛三等奖,全国中外诗歌散文邀请赛二等奖。诗歌作品《鼓浪屿之行》收入《中华诗词精选读本》(新诗卷)。
四十多年过去,我第一次回到了舅舅们和母亲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那就是我外婆的老家,踏上外婆老家的故土,自然也唤起了我童年初始的记忆。
在村中心,老樟树还是那样挺立,枝丫舒展,树叶葱蓉欲盖,绿荫下一块光亮留滑的青石还依然摆放在老樟树下,当年村民们出工前,外公拿着笨重的锄头就是坐在这块青石上,等待村长的一声号令。初夏的山村,风从山坳的那边吹来,风划过树梢,知了开始吟唱,整个小小的山村瞬间就有了女人的声音、有了男人们出工时粗狂的召唤,当然也少不了我们孩童撒娇、追逐和哭闹的声音。我的舅舅们、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童年都是在这小小的山村里度过的。
我三岁那年来到这里,现在想来记忆有些模糊,我只记得这里到处都是山,山连山、岭连岭,树木重叠,野鸟鸣翠。那一天,外公驮着我走了数小时山路,外婆用自己瘦弱的肩膀顶着挑子,晃晃悠悠的,两端是棉絮被子,后面跟着我的二舅,提着大小包裹,踢踢踏踏地随着外公、外婆的脚步,风尘仆仆地挪进了这座被山包围的小山村。刚到村口,我们受到村长和外婆几位娘家人的迎接,村长说:这是你们家的老房子,以后你们就住在这里。大家帮助卸下外婆肩上的挑子,外公把我放下,如释重负一般,外公说:还是家里好。
按照村长安排,我们就住在老樟树傍边近十几平方土胚墙的老房子里。据说老樟树有三百多年历史,也不知道经历过多少辈的人,老樟树在我的记忆里,它一直和周围山上的树木一样赋有浓浓的绿意。在老樟树东边还有一排近百十平米长条形的黄色土坯房,这是当时村里的集体仓库,也是村里最好的土房。在老樟树、仓库和我们住的土坯房的空旷地带,便是村里中心的集聚地打谷场,村民们通常把它叫做晒谷场。
到了村里的第二天,外公就跟着村里那些大老爷们一起出工,大家扛着锄头、提着弯弯的镰刀在田地里锄地、放水、割稻子。几天下来,外公显得有些腰酸背痛,体力活儿自然跟不上那些大老爷们。有一次,外公在割稻子时突然晕倒在稻地里,外婆的兄弟们都聚拢过来,把外公搀扶在长满杂草的田埂上,焦急地捶胸扒背,村长昂头看了看辣毒毒的太阳“呸”了一口唾沫,说:这鬼天气。他迅速让人从田埂边上取来了一瓢山泉水,一滴、一滴,滴进了外公的喉咙,外公在泉水的滋润下,渐渐地缓过一口气,望了望周围的人,吃力的眯缝着眼,缓缓地说:没事,没事,我,我能行。村长说:老兄弟呀,你就别硬撑了。村长的话说到一半,再没有吭声。外公和外婆的兄弟们,还有周围的那些大老爷们,谁都知道村长到底想说些什么。
从此以后,村里分配劳动,大家都抢着把最轻松的活让给外公干,在登记工分时,村长时常会默默无语地察看工分册子,登记册子的牛叔总会神秘的笑着说:大家放心吧,工分一份不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