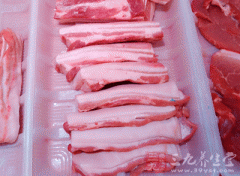漫谈中国古代情色诗歌:巫山云雨
性部之一:巫山云雨
李商隐《有感》:
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
古诗中涉及男女欢会的内容,常用巫山神女、云雨高唐之类的字眼,其始作俑者是楚辞大家宋玉,他在《高唐赋》中记述楚怀王游高唐时怠而昼寝,梦见神女自荐枕席,并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从此“巫山”、“云雨”、“高唐”、“阳台”、“朝云”、“暮雨”、 “楚梦”、“神女”等词就都语涉暧昧,不能随便使用了,正所谓“楚天云雨尽堪疑”。反过来,当言及男女欢爱之事时,这些字眼又为作者们提供了方便含蓄的说法。
怀王之子襄王也想学其父风流,与宋玉同游于云梦之浦,令宋玉赋高唐之事,日有所闻,夜有所梦,果然也与神女相会梦中,《高唐赋》的姐妹篇《神女赋》即记述此事。宋玉在此赋中极尽文字渲染之能事,描绘了一个尽善尽美、举世无匹的美丽女神形象。后人对神女念念不忘,不少文人加以赋咏,如建安时期的陈琳、王粲、应瑒、杨修等均有《神女赋》,曹植《洛神赋》也属此类作品。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大批香艳诗歌,其中有不少用楚王艳遇影射男女情事。梁武帝萧衍的一首《朝云曲》有句“复还没,望不来,巫山高,心徘徊”。《玉台新咏·卷十》载有一首梁简文帝萧纲的《行雨》诗为:“本自巫山来,无人睹容色。惟有楚王臣,曾言梦相识。”《艺文类聚·卷十八》载有梁元帝萧绎的一首《古意诗》:“妾在成都县,原作高唐云,樽中石榴酒,机上蒲萄纹,停梭还敛色,何时劝使君。”在萧氏父子带动下,梁朝许多文人都曾创作艳情诗,涉及巫山云雨,如沈约《朝云曲》,费昶《巫山高》等。南朝陈·江淹《休上人怨别》有“相思巫山渚,怅望云阳台”,江总《杂曲三首》之二有“阳台通梦太非真,洛浦凌波复不新”。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来,南北朝诗歌用楚王事,多是表现那种因佳人若即若离、可望而不可即而给作者带来的惆怅之感,与男女性事关系不大。
到了唐朝,巫山云雨在诗歌里出现的更加频繁了。初唐四杰都写过此类作品,卢照邻有《巫山高》,骆宾王有《忆蜀地佳人》,王勃有《江南弄》,杨炯有《巫峡》。王勃的《江南弄》如下:
江南弄,巫山连楚梦,行雨行云几相送。瑶轩金谷上春时,玉童仙女无见期。
紫雾香烟渺难托,清风明月遥相思。遥相思,草徒绿,为听双飞凤凰曲。
这首诗虽用了“巫山”、“楚梦”、“行雨”、“行云”等词语,但并非淫艳之作,表现的是情人相见无期,音迅难通,只好各自在清风明月之下遥相思念。
岑参《醉戏窦子美人》云:
朱唇一点桃花殷,宿妆娇羞偏髻鬟。细看只似阳台女,醉著莫许归巫山。
这首诗将美人比做巫山神女,但也不算淫诗,只是末句“醉著莫许归巫山”稍有一点意淫的味道。
李白有许多诗句,将美女和巫山云雨联系起来,如《寄远》十二首有“美人美人兮归去来,莫作朝云暮雨兮飞阳台”、咏妓诗《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有“楼中见我金陵子,何似阳台云雨人”、《清平调》咏杨贵妃有“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等。
李白《宫中行乐词》有“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纪昀评为“用巫山事无迹”(《瀛奎律髓·卷五》),因为“彩云”之“云”只是暗指“云雨”,把这个典故净化了。这种写法后代借用者不少,如晏殊《无题》“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晏几道《临江仙》“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姜夔《月下笛》“扬州梦觉,彩云飞过何许”及《鹧鸪天》“鸳鸯独宿何曾惯,化作西楼一缕云”等。贺铸《减字浣溪沙》是一首绝佳的闺怨词,有句“欹枕有时成雨梦,隔帘无处说春心”,说的是闺中女子在梦里能象巫山女神一样与情郎相会,而现实是残酷的,一道门帘将她与世隔绝,无处诉说她的怀春之心。张炎《长相思·赠别笑倩》有“去来心,短长亭,只隔中间一片云”,笑倩是歌妓,作者与其相别,感到怅然若失,因为她将象巫山神女一样飘然而去。
白居易有首著名的《花非花》,字词浅显但含义隐晦,算是早期的朦胧诗: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春梦”、“朝云”当指巫山神女,后人猜测此神女实为妓女,因为唐代妓女受召陪客,常是夜半才来,黎明即去。宋代贺铸《鸳鸯语》有“行雨行云,非花非雾,为谁来为谁还去”,显然由本诗生发。
纳兰成德《江城子·咏史》,也是朦胧诗,但用神女事更为明显:
湿云全压数峰低。影凄迷,望中疑。非雾非烟,神女欲来时。若问生涯原是梦,除梦里,没人知。
谈到朦胧诗,李商隐写了不少。“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义山的多首《无题》七律,具体写的是什么,众说纷纭。除篇首《有感》一诗外,他还有不少诗涉及云雨高唐,如《无题》“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叹自己如小姑独处,没有郎君可以依靠,“小姑”在此处指未出嫁的姑娘,语出南朝乐府民歌《神弦歌·清溪小姑曲》:“小姑所居,独处无郎”;《利州江潭作》“自携明月移灯疾,欲就行云散锦遥”,写龙与人交时,口含明珠,锦鳞皆张的威势;《楚宫》“朝云暮雨长相接,犹自君王恨见稀”,讽刺楚王的荒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