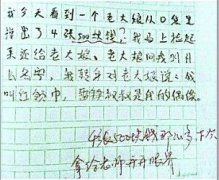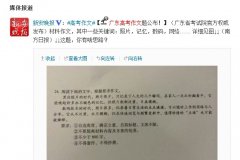《中国散文家》2015.5期“你是一条若有所思的河”(3)
那会,我还在中学念书。生产队的大老板子是我表哥,岁数比我长两旬多。每次拉废原油回来,他身上的衣服都造得油渍麻花、铮明瓦亮的。到队院子把马车卸完后,立马扛着大鞭回家“烀猪头”(睡觉)去了,待醒来时便是第二天的早晨。而每次,我都爱听他醒后咧咧的那一段扣人心弦的拉油故事。
油田的废原油坑很宽阔,像个缩小的盆地,又像个黑色的湖。油坑结构也很简单,上表面是一层黑油,约有十公分左右厚度,不知是冻的还是凝的,反正一块黑镜子似的镶嵌到坑里,直映出蓝天和日月星辰。板油下是一层冰,水深的地方冻得厚点,水浅的地方冻得薄点;有的地方干脆没冻,水面直接浮撑着黑色的板油。后来我知道,油田分油井和水井,水井要适时往出放水,而那坑里水便是水井里的水,还带有一定的温度呢。
在油田的地面布局上,有油井就带有油坑,叫贮油池。在几个油坑范围内,有个小白房,叫计量间。在计量间里值班的人,有男的,也有女的,有白班儿的,也有夜班儿的。进进出出的工人,都身穿着杠杠袄,脚蹬着翻毛鞋,头戴着狗皮帽子,如果不细瞅的话,还真分不出男女来。
表哥说,他们拉原油,常在晚上装车,都离小白房不远。一次累了休息,表哥在影风的小白房门前眯了一会。可哪想小白房的门是往里开的,人睡着了不能自控身体,身子一斜便把门倚开了,只听屋里“嗷”的一声,发出的是女人的声音。表哥忐忑中一个劲地道歉,可人家在惊吓平静后却十分大度,看表哥他们冻(也有吓的成份)得发颤的样子,便让大家伙到值班房里暖和会。
值班房取暖,烧的是天燃气炉子。在那时,油田职工住的干打垒,烧的都是原油或天燃气,连家雀都让油烟子熏出了黑色羽毛。表哥他们身上也很脏,一踩一地黑色原油印。可那女工并不嫌乎,在地上铺层砂子,为了打扫时好收拾地面。那一夜,女工没有休息。在早晨临下班时与表哥打招呼:“我也是农村来的,知道没柴烧的苦衷。”只这一句话,便一下拉近了石油工人和拉油农民的距离。
农村人憨憨的言表,折射出内在的质朴品格。在第二趟拉原油时,表哥从队上带些粘豆包、大黄米和一角猪肉。一是给分配油点的小队长些,让他再给分点好油坑;二是给那个女工点,表达一下感激之情。后来听说,在那女工结婚后,她家与表哥家还走动多年。那种纯真质朴的友谊,闪烁出那个时代的灿烂光辉。
当年拉原油,一趟往返需要四五天时间。表哥他们住宿选的地方,都是离油坑较近的屯子,存工具、草料、吃喝等等都方便。据说,他们在向阳屯、刘高手屯等地都住过。那时找房住是免费的,人家不要钱。都是农村人嘛,相互之间好沟通。
表哥还说过,拉原油必须配个铁管犁杖。我知道,这是表哥显摆自个儿发明的专用工具。油坑的原油,凝结一体成板状,用锹挖是很费劲的,有时拢堆火烧热铁锹挖,还能把速度提快些。当时,表哥联想到犁杖功能,便把犁铧卸掉按上割刀,一匹马在前边拉套,横竖几个来回,便把板油割成若干个小方块。这样,既省时省力,又提高了几倍的效率。
油田的冬天,虽然冰天雪地,油坑深处却还是冻不实的。偶有马蹄子踩到薄处,便会连人带马带犁都掉进坑底。水是不深,淹也淹不着,可寒冬的天气,一出水面就冻成冰棍了。就是那次拉原油,大表哥穿回一套杠杠袄裤、狗皮帽子和翻毛鞋,在屯子里到处炫耀,并一再澄清不是用马料换的。后来掌包的跟我说:“在那次掉水里的就是他,是那位女工管那位小队长要套杠杠工服,又腾出一会值班房让他换上衣服,要不呆会说不上会把人冻成啥样呢。”
记得那时,生产队拉原油,其间也就连续四五个年头,每年只拉三四趟。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拉原油的事便逐渐消失了。可是,每户农家的柴禾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那年冬天,父亲买匹马,与前屯温叔结伴到大庆捡原油。由于那咱油田把废原油都利用起来,各采油厂设置专业队伍回收,油坑也没有好油可捡了。当时,父亲是拉回一小车,但都是渣油(油渗的土),在灶坑里点不着呀。自生产队解体后,家乡才彻底摆脱烧柴的困难,土地全部分给各家各户,秸秆烧不了的烧,再也见不到庄稼人“锅下愁”(缺柴禾)的悲凉景象了。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一晃,告别拉原油的年代已有几十个年头了。今天,当我们走进富庶的乡村时,再也见不到拉原油的影子;当我们置身于广阔的油田时,再也见不到满坑废油的痕迹。可每当某一个闪念触动我敏感神经的时候,当年拉原油的往事便从遥远的记忆中浮现在面前。往事情节虽平淡无奇还有些苦涩,但总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怀念,在我心中鲜活、灵动地燃烧着,闪亮、熨帖地温暖着我的人生之旅。
交交黄鸟
◎ 李柯生
李柯生,又名李克生,大专文化,
读着“鳲鸠在桑,其子七兮”《诗经》之中的句子,正值早春之时,便听到啁啾之音。我仿佛看到了振翮而翔,跳跃桑榆枝条的黄鸟。它们向我们传递春的消息,为大自然增加欣欣生意。心情也逐渐从深冬沉寂中翻转过来,又被室外春旭融融,葳蕤姣姣所吸引,心就重归自然了,这大概就是人之本性吧。念着山野菜的味道,口内津液汩汩而生。于是,骑着我的踏板坐骑,直奔田野而去,大有不归之意。
采摘山野菜是我少年时就练就的本领,由于那个年代经常劳作,丰富了我鉴别能力。此时,在青青芳草之中,在山坡沟壑之上,拿着一把半尺长的尖刀,在草丛中寻觅。山野菜由于稚嫩,刚刚从土地里探出身子来,显得十分渺小,挖将起来颇费一番功夫。低头挖了许久,才看见袋子有膨胀之感。
挖到一片芦苇丛生的垄地,大概是土地荒芜的缘故,粗壮的芦苇把山野菜欺压得瘦小羸弱。我一边拨开芦苇,一边费力的寻找。看到一片一片的苣荬菜,像是患了营养不良症的婴儿,有气无力的依偎在芦苇下面。看来,芦苇绞杀了它们,这就是植物之间的一场战争。我就用尖刀一划,苣荬菜连叶带根剥离开土地,被我用手一一捡拾起来,放入袋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