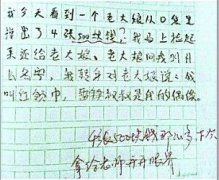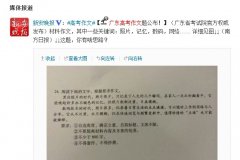《中国散文家》2015.5期“你是一条若有所思的河”(7)
还有痴男怨女,儿女情长。“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映衬《新乐府》中思妇孤枕难眠的寂寞;“墙头马上,漫迟留,难写深诚”“道出《长相思》中商女芳华自怜的哀怨;还有“敛着眉儿长叹,惹起旧愁无限””的柳永,在《秋月夜》中亦难排对情人的无限眷恋。
“千里江山昨梦非,转眼秋光如许”。明代画家文征明在《念奴娇•中秋对月》中,踏上想像的翅膀,“欲跨彩云飞起”,直达蟾宫折桂,享受歌舞升平的欢乐,不料却又跌入“莫负广寒沈醉”的烦恼,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差距,表达得这么酣畅却又那么无奈。
还有“风雨满城,何幸两重阳之近;江山如画,尚从前赤壁之游”。坚贞爱国、褒涵节义的文天祥即便在日常乡饮《回董提举中秋请宴启》中,也充分流露出对祖国壮美河山的赞誉、挚爱和坚守之情。
饱阅世事悲欢,乐观进取向上,最有力感的还属公元1076年中秋之夜,苏轼于密州(今山东诸城)的典范之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其高逸舒放的词风意境,宠辱忘外的人格力量,都跨越了千年的明月,奋勇激越,光耀后世。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类的足迹已经登临了月球并迈向深远的太空,仰望苍穹,或许我们已少了古人那种热切和冲动。但烟波浩缈的宇宙毕竟还有更多未知的领域等待我们去研究、探析、开发和利用。
仰望明月,不知您又作何感想?
亿兆观是月,念感竟相殊。
斗转随河汉,浩宇一物沙。
笋溪竹鸡[外一篇]
◎ 钟治德
钟治德,1964年生,重庆市作家协会、杂文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作品见于《小说月报》《散文百家》《中国散文家》《文学月刊》《杂文月刊》《杂文选刊》《散文时代》《散文选刊》《中外文艺》《散文》《随笔》《野草》等期刊。
故乡的笋溪翠竹连天匝地,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笋溪的鸟,都与珍禽扯不上关系。竹林的边缘,就是农人的家园,翠竹夹岸的河道,是水上讨生活者的领地。四周青山静立,宛若画屏。笋溪流域最常见的竹鸡,就在流水与竹林间出没。碧水绿茵茵的,翠竹绿茵茵的,竹鸡也裹满了笋溪的绿意,笋溪子民对竹鸡的态度,其实也出自一种纯然的底色,犹如临水而居的生民,对最美的白云和最美的月白习以为常。
竹鸡形似鹧鸪,上体橄榄色,腹部浅棕,两侧有许多黑斑点。在鸟类大家族中,竹鸡算不得俏丽,大约是沾了“鸡”的俗气,所以不是飞翔的健将。竹鸡在竹林下悠闲地觅食,个体发现了美食,必停下来,顿一顿并非颀长的脖子,播送出“呼咕呼咕”呼朋唤友的清音,音符之间拉开间隔距离,由气息去连贯,就像和风吹送的泉鸣,柔柔扩散开去,就有了笋溪风月之酷。受到感染的竹鸡,纷纷赶赴盛宴,群集在一起,雄竹鸡亮开漂亮的彩羽,很绅士化的派头,在一旁担任卫士,看着雌鸡们进食。
竹鸡喜食竹林沙地里生长的竹叶菜,一种浅灰色的野菜,叶片如竹,一簇一簇牵牵连连,俨然缩小了的竹丛盆景。出现了险情,那卫士扑地一声飞上竹枝,发出警号,“呼咕呼咕”的清唱此时缩略为“呼咕”的短促啼鸣。群鸡“轰”地四散飞开,那绅士派头的卫士总是最后一个离去,绅士就成为勇士。竹鸡离地数尺,费力扑楞翅膀,激起竹叶沙沙直响,竹枝随着闪动,像小船划开绿波。
这种竭尽全力的飞翔,距离最远不过十余丈,续飞能力十分有限,竹鸡就气喘吁吁斜斜坠落地面,躯体滚了几滚,头部扎入草丛刺笼,尾巴却还露在外面一翘一翘的。这种顾首不顾尾的藏身法子,很可怜,也很悲壮,竹鸡因此常被人活捉。捉竹鸡的人,不要任何工具,随身只携带一只布袋或者一个竹编的大鸟笼,悄然隐身在竹丛中,眯了眼,竖起耳朵听竹鸡的声息,以经验判断竹鸡的多少,选择出击的时机。时机到,蓦然蹦出来,“荷嘿”一声狂呼,立刻搅起竹林下的仓皇逃遁。竹鸡们喘息未定,厄运降临,一只一只被掐着尾巴揪出来,塞进口袋和鸟笼里。
这捕捉的法子实在没有精彩的技术含量,捕者自称为“拣死鸡儿”,极度藐视了竹鸡这种林下生灵。这句土语流出了笋溪,撒播在巴蜀大地,有清清浅浅的知音共赏,巴蜀人讥评不费力就收获了好处,就用笋溪长出的这个俗语。知音能有几回赏?虽然少有人关注笋溪流域的方言现象,但是毫不妨碍它做余兴未尽的歌者,以永远跳跃的音符,诉说着幽梦。
竹鸡的这种际遇,或许让人同情,于是笋溪流域流传“捉地麻雀”的游戏,大人小孩同玩。地麻雀是竹鸡的土名。游戏分为双方,一方是“人”,一方是“鸡”。“人”是个体,用“石头剪子布”的方法确定,其余参加者为“鸡”的群体。游戏从践踏人性开始,“鸡”们拉着手,连成一个圆圈,把被黑布蒙了眼睛的“人”圈定在圆心,圆圈快速转动,愈缩愈小,把“人”围困得团团转,“鸡”们朝“人”哈气,叫“吹风”,朝“人”喷唾液,叫“下雨”,往“人”的屁股踢去一脚,叫“打雷”。“人”终于被“鸡”们折磨得够呛了,于是“鸡”群的首领,用一种苍凉的声调,吟唱“地呀地麻雀,麻雀麻雀飞”,连续三遍,第三遍的“飞”音一断,“鸡”们立刻松手,四散后退开去,蹲在地上。“人”半蹲状,作青蛙跳,开始扑“鸡”,“鸡”不能站立,蹲着巧妙躲闪。躲闪其实就是“鸡戏人”,“人”左边一扑,“鸡”往右边一闪,“人”的一扑,往往成为哄笑中的“狗啃屎”。总有不幸的“鸡”被人扑住,于是就去当“人”。悠闲的夏日和冬闲之季,这种群体游戏总是在古老的笋溪两岸无休止地上演着,驱走了寂寞,换来郁闭中的勃勃生气。“人”在游戏中成为弱者“鸡”的奚落对象,游戏中人以当“人”为运气不佳。这种古老的游戏起源于何时?不知道。其意义的指向,是人的忏悔?还是人对自然万物的感恩?诸如此类,尽可以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