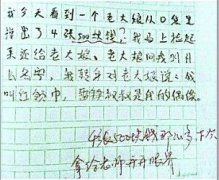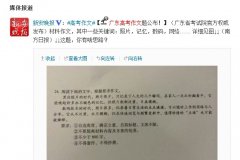《中国散文家》2015.5期“我见故乡多妩媚”(9)
翻过老屋苦涩的一页,轻轻开启老屋欢乐的时光。我清楚地记得,春天的老屋是最富有生活趣味的。当清脆悦耳的柳笛声从窗口欢快地飞进老屋,把冬的寒气一股脑儿挤走之时,我便甩掉棉衣的束绊,急猴般地冲出老屋,和伙伴们颠跑在六郎堤下那返青的麦田里放风筝。随着风筝慢悠悠地在空中越升越高,心里那个美啊,仿佛我们那一颗颗醉透了的童心,也被三月剪剪轻风送上了瓦蓝瓦蓝的天空里。那如醉如痴的感觉,永远蛰伏在我心灵的深处不会消失。
夏日黄昏,袅袅炊烟笼罩了老屋的房顶,已是薄暮冥冥时分,父亲还在田间劳作。我光着脚丫,溜出老屋,坐在村口菜园里的那棵歪脖老柳树上,向父亲劳作的那块庄稼地张望,盼望着父亲快些收工回家。炊烟由浓逐渐变淡,屋檐下便会飘来姐姐长一声短一声催我回家的呼唤。
皓月高悬中天,月光撒满草垛和老屋房顶。我依偎在父亲的怀抱里,在院子里听纳凉的大人们谈古,讲鬼怪故事。一堆用于熏蚊虫的麦秸燃在院落边,不时发出秸秆爆裂的脆响。祖父的旱烟袋忽明忽暗,像萤火虫一样,点点星火点缀在夜空里,一晃就不见了,留下的依旧是月光泄下的苍白。夜深了,串门聊天儿的大人们都已回家,父亲把入睡的我抱进老屋,月亮也悄悄地从窗口跟进来轻抚我的脸。我至今记得,父亲坐在炕沿上,为我轻轻摇着蒲扇,摇下缕缕柔风,摇落串串歌谣,落在我的枕上,飘进我的梦里。
雨天的时候,我会静静地坐在老屋门口,看密密麻麻的水滴自房檐一串串急涌而下,似断线的珍珠,砸出地面簇簇旋转的水泡儿。后来读到唐代诗人王建的《听雨》:“半夜思家睡里愁,雨声落落屋檐头。照泥星出依前黑,淹烂庭花不肯休。”我总会想起儿时坐在老屋门口看雨听雨的情景,也更加唤起我想念家乡的情怀。
最惬意的事情是跟着姐姐去河边洗衣裳。姐姐用木棒槌在青石板上卖力的捶打拆洗的衣物,那“咣咣”的节奏声就像今天的打击乐。河水清澈见底,可以看得见成群的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只是人一靠近,便四散奔逃了。姐姐洗衣裳的时候,我会在河坡上的草丛里捉蝈蝈,逮吱蚂蚱。姐姐洗完衣裳倘若时间允许,也会挽起裤腿在河边捉鱼,沿着有水草的浅滩探摸一遭,就能捉到活蹦乱跳的鲫鱼瓜和小虾,回家后就会变成我饭桌上的美餐。
冬天,大雪封门的日子,漫漫长夜里,呜呜的西北风扯天扯地的吼叫着,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取暖,听父亲讲他小时候的事情,那乐融融的感觉真的好甜好甜。大姐似乎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在昏暗的煤油灯底下搓麻绳,纳鞋底,做鞋子。要知道,大姐那时也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姥姥家居住时,就已经跟姥姥学会了针线活。大姐用自己的一双巧手,温暖了全家人的生活。
物质极度贫瘠的年代,春节,在我们童年的翘首期盼中,总是姗姗来迟。然而,年,终将会在我们计算天数的小手指尖上一天天靠近我们。随着爆竹声此起彼伏地在大街小巷噼啪炸响,年,终于欢蹦乱跳地落在我家干干净净的院子里。肉香漫过父亲忙碌的灶台,弥散在老屋的上空,萦绕在我们渴望的小嘴边,飘荡在我们欢跳的童歌里。我早早就穿好大姐缝的新衣,做的新鞋子,等着吃饺子,放鞭炮,给院子里的长辈们拜年。拜年是件高兴的事,因为磕头可以得到压岁钱,少则两三角,多则五六角。那时的一角钱可以买几支铅笔,也可以买几个习字本,当然还可以买到一本小人书。平时,父亲从不给零花钱,我们也没有要零花钱的习惯,只是在读小学交学费时,才会向父亲讨要。
在漫长的几乎没有止境的岁月里,我的父亲拉着早已超重的车,拼命朝前赶。为了搬出狭小的老屋,给他的儿子盖一栋宽敞明亮的房子,父亲把自己变成了牛。从春干到夏,又从秋忙到冬。皱纹像一条条虫子,爬满了他的额头,白发像一根根蚕丝,绕满了他的头顶。
父亲,收割着我们,岁月,收割着父亲。
时光流转,岁月匆匆。而今我家的那处老屋,早已被留守在那个宅院的老婶和她家的孩子们糟蹋的成为残垣断壁,我藏匿于老屋的那些尘封旧事,也只能在梦里找寻了。
三
不堪回首的往事一旦回首,就会引来一阵揪心的伤痛。
我家现在的一栋老屋,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几乎耗尽了我父亲的一生心血。
故乡有个习俗,凡是做了父亲的人,不论穷富,都要有一个几乎耗尽一生心血去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能给儿子盖一栋房子,为的是好让儿子娶妻生子,延续香火。
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盖一栋房子,对于土里刨食的农民而言,绝非是一件易事。有为此举家外出沿街乞讨的,还有的为此攒钱而节衣缩食饿昏过去的。故乡的每栋老屋里,都会有一个凄楚的故事。
我的父亲为了攒钱购置砖瓦木料,垫房基没舍得请本家帮工,硬是凭着春燕衔泥垒巢般的意志,用一付筐蓝儿,一条扁担,一挑一挑地往宅基地里运土。担了不知多少挑的土,磨秃了多少把铁锹。每天从鸡啼破晓开始,到夜晚繁星点点收工,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拉犁翻地的黄牛。
终于,在一个豌豆花开,小麦抽穗的时节,父亲的新屋落成了。
新屋落成那天,父亲拿出一挂鞭炮让我燃放。听着噼啪爆响的鞭炮声,父亲像个孩子似的笑了。望着父亲疲惫消瘦的面容,我却偷偷地哭了。
在父亲盖的房子里,我的三个姐姐相继出嫁。父亲的房子里一下子冷清了许多。
我师范毕业,回乡做了一名教师,娶了善良贤惠勤劳能干的妻子。而后,我的可爱的女儿和聪慧的儿子又先后出生了,父亲的屋子又一下子热闹了起来,父亲满脸都是笑纹纹。父亲曾经给我唱过的歌谣又被我的父亲唱给了他的嫡孙。父亲一直没有续弦,把自己一腔赤诚圣洁的爱无私的奉献给了我们。
父亲晚年时脾气异常爆裂,有时,就像一堆干透了的柴草,哪怕遇上一点火星儿,都会熊熊燃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