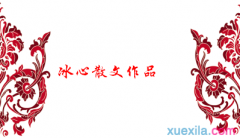【尘世物语】华夏散文2016(6)
董阿婆是个很硬气的老人。当初生产队要把她作为“五保户”报上去,她死活不肯。我们村里还有一位老人,年纪和她差不多大,也没有儿女,村里定她为“五保户”,每月的口粮都是定期供应。可董阿婆却坚持自己出工,分田到户后又带着傻儿子耕田种地。开始她的儿子什么都不会做,董阿婆就把他带在身后,手把手教他。春插时教他拔秧,夏收时教他割禾,可是像耕田、插秧这些带技术的活儿她自己都不会,就没法教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扛着锄头,弓着腰,一又小脚迈着细碎的步子,走在晨露未晞的田埂上,走在骄阳炙烤的坡地里,而在她蹒跚步伐的身后,总是跟着一个走路摇晃、呼哧喘气的汉子,这已经成了我们村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那时,田里的活并不多,最多最累的还是地里的事儿。我们那个小村庄四面环山,这些小山有一半被开垦出来了,一半还是树林。那些坡地非常肥沃,种什么都有好收成。所以,一年四季,这些坡地都和村里的人一样,闲不着。春天里,田野的冰雪刚开始解冻,董阿婆就带着根上山去挖地,准备种大豆、种花生;豆苗像小鸡那样挣破蛋壳探出头来时,董阿婆又带上根去锄地。立夏以后,董阿婆又要带根到坡地里去栽种红薯秧,等薯秧刚开始蔓延,她又带上根去锄草、施肥;夏天,地里的大豆收割了,又要忙着种玉米;秋天,玉米收起来了又要忙着种油菜、种荞麦、种蚕豆……地一天闲不着,董阿婆和根也一天不得消停。刚开始,被董阿婆磨得亮眼的锄头总是欺负根,不是把豆苗和杂草一起腰斩了,就是把根的脚割得鲜血淋漓,痛得根呲牙咧嘴,口里一个劲地“呀呀”乱叫。董阿婆一边大声呵斥根,一边抄起一把粘土,敷在根流血的伤口上。根不喊叫了,又开始弓着腰锄地,而董阿婆却悄悄地背过身,眼泪扑嗒扑嗒地掉进地里,这一切,只有地里疯长的庄稼看得见。
三
在村里,没有儿女的老人就像路旁的一些草芥,自个儿生自个死。董阿婆不想做这些野草,所以她就抱养了根。把根拉扯大了,她又在想着怎样让根也留下“根”来。一晃根就差不多三十出头了,可能够让根耕种并留下根苗的土地却还是影儿都没有。这可愁坏了董阿婆,一头白发越发抢眼了,像一蓬蓬盛开的荞麦花。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邻村有一个叫春秀的姑娘,也和根一样痴呆的,媒人上门一说,她家里就同意了,根就娶了一个和他一样呆傻的老婆。据说进门的那个晚上,董阿婆像教根种庄稼一样教会了根去开垦那块荒芜的土地。
春秀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从来不会笑的根也会见人就傻笑了,董阿婆更是一张老脸笑得像绽开的菊花。可好花不常开,九月初的一个深夜,春秀的喊叫声惊起了全村的犬吠,村里的女人都赶到了董阿婆的那个黑暗的房间里,接生婆也摸黑赶来了,春秀毫无规律的喊叫揪住了所有人的心。到天快破晓时,春秀终于停止了喊叫,可生出来的孩子却是一声哭叫都没有,是个死婴。董阿婆当即老泪纵横,这一回,她的眼泪想藏都藏不住了。她用一张旧床单裹紧了婴儿,声音哽咽地央求我细母舅把他抱到后山埋了。一夜之间,董阿婆又老了许多。
以后的几年,春秀就像后山肥沃的土地一样,接二连三地被要根下了种子,可接二连三地结出的果子不是先天死亡的就是后天夭折。唯一有过一次,她生下一个女儿是活的,而且眉清目秀,一点都不像她和根。董阿婆像在薯地里捡到了一棵灵芝,把她含着嘴里捧在手心。小姑娘长得白白胖胖,一岁多会下地走路,会开口叫“婆婆”,逗得董阿婆眉开眼笑。可到四岁的时候,有一个晚上小姑娘突然发烧,还没挺到天亮,就突然人事不省。等董阿婆声嘶力竭地唤醒邻居时,小姑娘一声婆婆都没叫就走了。董阿婆哭得背过气了,根、春秀也哭得眼泪鼻涕满脸都是。醒来后的董阿婆一言当发地拿出小姑娘最爱穿的衣服,细细地跟她换上,再央人用松木板做了一只小棺材,请人抬着埋在自家的祖坟边。
大痛过后的董阿婆,经常神思恍惚地来到她孙女的小坟边枯坐。村里人有时半夜醒来,都会看到后山的坟山上,有一个沙哑苍老的声音在低低啜泣,惊起的夜鸟哀呜着飞过那片黑漆漆的松树林。
春秀在根无边的耕种和无数次血泪的分娩中,慢慢地衰老了。她的脸比黄土还黄,她的身子比芭茅还瘦。终于,在一个雨夜,在又一次痛苦的分娩中,她和肚子里的孩子一起走了。
这一间黑暗的仅留有一个口子形窗子的老屋内,又只剩下董阿婆和根了。一切,又回到了从前。
四
疼痛就像地里疯长的野草一样,在董阿婆的全身蔓延。
前几年,她的一口牙齿还可以崩得碎蚕豆,今年以来却慢慢掉光了,头上的白发已盖不住薄薄的头皮了。她的手半点力气都没有了,不说拿锄头,就连拿把菜刀都没劲,而且全身的关节、筋脉都在疼痛。
村里另一个老太婆早在十多年前就走了,只剩下她一个老人像秋天枝头上最后一片叶子。秋风一天紧似一天,这片瑟瑟发抖的叶子,也快要归入土地了。
疼痛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的,董阿婆已记不清了。是十多年前孙女离去的时候,还是春秀走的时候,她真的记不起了。根更不知道。没有了春秀,根的力气全都使到田地里了,每天吃饭都不晓得回来。烈日炎炎的中午,董阿婆颤巍巍地站在村口,两手拢成嗽叭状,向着根劳作的地方,大声呼唤:
“根啊,回来吃饭呀——”
直到群山汹汹地回应,根才掉转头,看见了老娘的身影,他就摇摇晃晃地往回走。
可是,近来董阿婆觉得喊的力气都没有了,饭也做不好了,有时只能熬些粥。根什么都不知道,他每天照样下田下地。直到有一天,根发现董阿婆躺在床上起不来了,才慌慌地出去找人。跟他邻居的是我细母舅和表兄,表兄出外打工了,家里也只剩下母舅和舅母两个老人。村里所有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老人的疼痛在村里已是司空见惯了。比如我母亲的关节痛,我叔叔的肺气肿,我舅舅的风湿病,他们的疼痛和呻吟在山村的暗夜里蔓延。根学会了做饭,也慢慢地懂得了喂董阿婆吃些东西,董阿婆躺在床上,由于没有人料理,身上到处生起了褥疮,已开始溃烂。到后来,衣服都穿不上身了。
疼痛。疼痛。她全身到处都在疼痛。
整个村子里,到处都是疼痛。
1979年的疼痛
记忆中的疼痛是1979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