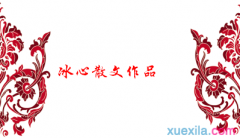【尘世物语】华夏散文2016(7)
疼痛来自我的右手。那是一个少有的晴朗的上午,生产队的男女老少40多号人正在搞“山光”(我们那里的田是一梯梯的,田墈高,每年春天都是把田墈里的茅草清除干净,就像剃胡子一样,谓之为搞“山光”)。社员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就像田野里闲散的牛羊一样。那时我和几个小伙伴正在玩百玩不厌的“打仗”游戏,我们正在发起冲锋,在一座几个人高的田墈前,别人都愣住了,只有我英勇地义不反顾地跳下去了,只觉得眼一黑,趴在地上就不能动弹了,接下来就觉得一种尖锐的疼痛从右手传来,整个人就像一条黄泥鳅在泥地里翻滚。那些劳作的大人吓住了,赶紧围拢来,把我抱起。我的右手无力地耷拉着,钻心的疼痛一阵阵袭来。我躺在门板上,等待着乡间跌打医生的到来——早有人飞跑着去请医生去了。当时,在穿过一座山一条小河的另一个村庄,我们大队支书的女儿冬瓜的手也摔折了,正请了跌打医生在接手骨。隔着山崖和河流,都能听到冬瓜像牛牯一样的嚎叫声。那位医生飞跑着赶来了,他不顾我的疼痛,对着我红肿的右手臂左看右捏。良久,他转过头大声叫人去拿绳子。我二哥赶紧找来一根系牛的麻绳,医生示意将我捆在床板上,我痛得无法说话,无法哭喊,汗珠子像黄豆一般从我的额头涌出来。医生双手将我的痛手使劲抓住,一捏一拉,只听细微的“咔嚓”一声,断茬的骨头接上了。他快速地拿起两块夹板,轻轻地挟在我右手小臂的两边,再用布带子一道一道地绕好、绑住。这种情形,就如同是在进行果树嫁接,我的右手还会长成原来的样子吗?这成了我整个童年最大的担忧。手的疼痛逐渐减少了,可另一种疼痛却又开始了。
这一次的疼痛是痛在我舅舅一家人的心上,我漂亮的大表姐竟然跟人跑了。舅舅那时已有五十多岁了,刚刚经历丧妻之痛,现在又要罹受失女之悲了,本来就稀稀疏疏的头发一夜间掉的掉,白的白了。说起我的大表姐,那可是村里最美的姑娘,人美,手又巧。她经常到我家来,和我大姐住在一起。她们两人最拿手的话儿就是做布鞋,做衣服,两家人的鞋子、衣服都是她们做出来的。我姐做的鞋比表姐的要好,表姐做的衣服比我姐的式样要新。她们两人都是无师自通,经常在那间幽暗的房间里裁呀剪呀,忙个不停。那时家里没有缝纫机,那些衣服和鞋子都是靠手工做出来的,经她们两双巧手做出来的鞋子,针脚又细又密,穿上又暖和又舒适,衣服更是漂亮。我记得表姐自己缝制的一件杏白衬衣,衣领的两个尖角又尖又长,像两只翩然的蝴蝶,美丽极了。可是,我的这么一个心灵手巧、美丽聪慧的表姐竟然跟人跑了,叫人怎能不痛心呢?
疼痛压得舅舅一家喘不过气来。更让人心痛的是,表姐竟然是跟一个“温州佬”跑的。那年的春天,我们村子附近的一座水库要改建为电站,可这个水库的蓄水量不够,要从另外的一条河里引水过来。引水要架一条几百米长的渠道,要凿一个山洞,有一伙温州人包下了这项工程。他们先是要打通这个一百多米长的山洞,这个山洞穿过的是一座岩山,全部是坚硬的岩石。每天天刚亮,他们就开始凿山洞,先用锤子和钢钎凿几个眼,再把炸药填在里面炸。他们打钎时非常好玩,高亢而有节奏的号子,准确而又迅猛的锤击,随着纷飞的石屑传遍了整个小山村。我们这些小孩最喜欢看他们干活,有两个小伙子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最深。他们赤裸着上身,打锤时手臂上的肌肉就像两只灵活的老鼠上下窜动,完全可以用今天的“酷”字来形容,把我们都看呆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美丽的大表姐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也爱看那些像老鼠一样飞窜的肌腱。
我们这个小山村一直没来过外人,这些温州人的到来引起了全村人的骚动与好奇。每天,他们顶着一头白蓬蓬的石屑回来,眉毛、脸蛋和赤裸的上身,都是一层白蒙蒙的尘土。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他们洗澡也不跟我的坐在一个大木盆里一样,而是提着一个铁桶来到水井边,舀满一桶水从头到脚地浇。吃的更与我们不同,我们不敢吃的蛇,他们也捉来吃,还喝从老远的县城买回的酒。我们尝过,味道好酸,像泔子水,他们说是啤酒。有两个温州人借住在我家里,他们总是跟我们说起自己的家乡温州,那里有蓝天一样宽广的大海,有林立的高楼和烟囱……我表姐经常到我家来玩,时常一副听得入迷的样子。后来她和其中一个健壮的小伙子跑了。
舅舅没念过书,小时腿瘸,学了一手的剃头手艺,常年背着剃头箱子四村八岭地跑。那一天,他从外地回来,揭开锅盖,锅里什么也没有,连灶台子也是冷的。他到处喊表姐的名字,一路喊到我家里来,没有听到表姐的半点回音。寻遍了村里十三户人家的每一个角落,也没见着表姐的影子。
那一天,我的右手臂不知怎么又疼起来了,而且还红肿、发烧。母亲顾不上去帮着寻表姐了,她四处去寻找跌打医生。跑了十几里山路,她打听到红光小学有一位姓彭的老师会接骨,她就赶紧去请彭老师。彭老师是个下放知青,那时还没回城,经不起我母亲的眼泪和絮叨,跟我母亲到我家来了。他解开我手上的布带子,仔细地看了看伤口,说是骨头没接正位,要把骨头拉断,重新接。我一听就嚎啕大哭,说什么也不肯再接,彭老师叫我大哥、二哥又用那根牛绳把我捆在一把木椅上,凶狠地给我接骨了,我只知道一阵钻心的疼痛……
等我醒来,已是掌灯时分了,屋外一片黑暗,只是不断传来我舅舅焦灼而又沙哑的呼唤声。那一夜,舅舅凄厉的呼唤声和我尖锐的痛楚在我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回荡。
天还没亮,舅舅就出门寻找大表姐去了。他背着一个蓝布包,这布包还是我表姐亲手缝制的,上面绣着一朵荷化,两只交颈相戏小鸟,非常漂亮。他一踮一跛地从我家门前的小路上匆匆走过,只听见几声尖锐的犬吠。母亲也起床了,隔着窗子对着外面的黑暗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们都不知道,舅舅还能不能把我美丽的大表姐找回来。我的手又隐隐在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