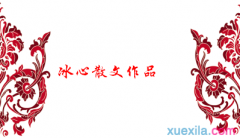【尘世物语】华夏散文2016(9)
夏雨初晴,空气湿润润的。村子里的小姑娘,挎上竹筐,结伴去野外采摘黄花菜。风也摇摇,人也摇摇,小姑娘们迈着细碎的步子,走向一片萱草地。地面湿湿的,可以光着脚丫,一步一个脚印,那个季节里,脚印也生香。萱草的草心,拔出一根根花絮,每一根花絮上,都有四五朵花簇在那儿;有的已然开放,有的正处花蕾。开放的,如一支支举向天空的金黄小喇叭,仿佛,执意要把天空吹出一片明朗。花心里缀了水珠,把碧蓝的天空,也收进花心里。姑娘低头去看那黄花,晶莹的水珠,便映出了姑娘的笑颜,姑娘笑得愈加灿烂。手指葱白如玉,食指和拇指轻轻一掐,一朵黄花就开在了指尖上。要轻,不能重了,小姑娘懂得一朵花的痛;可是又不能不掐,萱草花虽然美,可生命太过脆弱,短暂的只有一天的时间。
若不及时掐去,花就败了。败了的花,萎落尘泥,徒然叫人生一份伤感。
似乎,所有娇美的事物,都注定了生命的短暂。
采采复采采,萱草地里,小姑娘们左采右采,采来采去,轻快如翻飞的蝴蝶。夏日明媚,黄花映衬之下,小姑娘的脸,似乎更加明媚。嬉笑宴宴中,所有的忧愁,都抛到了云霄之外。烦恼,不属于这个季节的,不属于少女时代的。或许,在这些小姑娘们采摘黄花的同时,也把快乐和母爱,采摘进了自己的内心中。
待到成年之后,“坐北堂”的时候,便就母爱泱泱了。
古人寝室的编制,分为前堂后室,由室而之,内有侧阶,即所谓北堂;每逢祭祀,主妇即位于此,所以,北堂属母亲所居之所。古代,母亲居住北堂,庭院中,又常常种植萱草,故而,北堂亦称之为“萱堂”;自古以来,“萱堂”也就成为了母亲的代称。萱草,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母亲花”。
《诗经•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就是表达的这个意思,也许,还是最早表达这一意思的诗文。王冕《偶书》:“今朝风日好,堂前萱草花。持杯为母寿,所喜无喧哗。”王冕的这首诗,则另有祝母高寿的含义。
想那一日,一位母亲坐于北堂之内;庭院中,萱草花开,流光散溢,浮泛荡漾,一派绚丽的璀璨。萱草花,多呈橘黄或者橘红色,都是那样的饱满、醇厚,都让人觉得可爱。那母亲静静地坐着,仪态端庄而安详。她的眼睛,望向庭院,望向庭院中正在开着的萱草花,看着看着,记忆就回到了她的童年,童年中她手挎的那只竹筐,泥地上留下的那一行行脚印,还有回家后,母亲的母亲做下的那道“黄花菜”……
于是,她笑了。平和而安静的笑,满足而欣慰的笑,那么深醇,而又那么慈爱。我相信,所有的母亲,在现实中,或者在内心里,都演绎过这份内蕴的笑。
“蕙洁兰芳,华而不艳,雅而不质”,有蕙草之洁净,有兰花之芬芳;华贵而不俗艳,典雅而不朴陋,古人对萱草有如此之评价。今天看来,这种对萱草的评价,实在也是对母爱的一种最好的诠释。
自古美人多受眷顾,也往往被赋予更多的雅号,或美称。
萱草不是美人,但却是美草,所以,亦是美称多多。萱草、金针、黄花草,它还有一个直抵人的心灵的名字:忘忧草(或者叫“疗愁草”)。
曹操说:“何以忘忧?唯有杜康。”曹操之“忧”,有儿女情长,但更多的却是“忧国忧民”,是一种“大忧”,所以他端起酒杯,慷慨豪饮,大丈夫之性情,气贯长虹。而萱草之“忘忧”,我总觉得,似乎更偏重于“儿女情长”,纵是母爱,到底也还是“儿女情长”;所以,唐朝•孟郊,才在《游子诗》中写道:“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堂门,不见萱草花。”像他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一样,丝丝线线,花花草草,都寄寓着对母亲的一番思念。
宋人王十朋,有诗曰:“有客看萱草,终身悔远游。向人空自绿,无复解忘忧。”所表达的,也无非是一种思乡、思家之情,之忧。
不管怎样,萱草之“忘忧”,到底有了一份情。
把“忘忧”之情,蕴于萱草之中,就赋予萱草一种形而上的东西;使这朵金色的花朵,盛开在了人们的血液中,成为了一种绵延不绝的民族情感。
低矮的萱草,也因此有了一种更高的生命高度。
灰灰菜
提及灰灰菜,我首先想到的,倒不是灰灰菜本身,而是大片的成熟的小麦。
还是大集体时期,我也只是一名小学生。众多社员手挥镰刀,在前面收割小麦,我们这些小学生,就跟在后面,搞“复收”一一捡取落漏在地面上的小麦。
劳动一段时间后,中间要休息。一到休息时间,我就满地里跑着,寻找灰灰菜。临出坡时,母亲曾千嘱咐万叮咛:“别忘了拔灰灰菜。”因为,灰灰菜决定着那一天全家人,午饭或者晚饭生活的改善。
日子贫穷,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几棵灰灰菜,就可以熬一锅“灰菜汤”,在那忙碌、劳苦的麦收时节,得以为全家人佐餐。
大片的小麦,一地金黄。风起时,麦浪滚滚,麦香肆意地散溢着,热浪裹着麦香一阵阵扑向脸面,像肥胖的女人的体香,粘稠而醇腻。我顾不得天气的炎热,在田垄上奔跑着;眼睛,直直地盯向前方,寻找着那一点点的绿色。那是一种充满诱惑的绿色,直接透进食欲的深腹。灰灰菜,是耐旱的植物,尽管天气炎热,它却依旧青灵灵地绿着;在满地的金黄中,那点绿,就格外地醒目。麦田肥沃,生长的灰灰菜,也格外肥大;而每寻找到一棵灰灰菜,就给我的心灵带来一份极大的欢喜。